今夜無月,有風(fēng),高高密密的竹林,竹葉嘩嘩作響,我在這一片漆黑里不知摸索了多久。
鎧甲里側(cè)腰的傷口還在流血,順著內(nèi)衫向下流淌,怕是傷著內(nèi)臟了,格外疼,與之相比,腿上和胳膊上的傷沒了感覺,血流的太多,要盡快找機會包扎一下。
只是還不能停,他們離得不遠,遲早能發(fā)現(xiàn)出了岔子,追上來就麻煩了,今夜,必須翻過這座山去,翻過去,跨過河,就安全了。我加快了步伐,傷口更疼了,這身兵甲真的是沉,好想脫了去,只留刀,不過路還長,還不是時候。話說,這竹林到底在山的什么位置,我怎么沒有一絲印象。
在竹林中走了大約快一個時辰,快虛脫的時候,遠處有星星點點的光透過來,風(fēng)里飄來一絲絲的笛音和人聲。
我停下來,沒有馬叫嘶鳴,應(yīng)該不是他們,沒這么快。我緩緩的向前,不遠處,竹林道側(cè)旁,生著一大堆篝火,篝火旁圍坐著幾個人,有人正在吹著竹笛。我抽出腰間的佩刀,一步一步靠過去。
笛聲戛然而止,火旁一共四人,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呆呆地看著我,剛剛吹笛子的是個小姑娘,此刻正努力把自己藏到老者身后,深夜忽然冒出一個渾身是血拿著刀的大漢,害怕也不意外。
似乎是尋常百姓,我稍稍安心,老者起身作揖:官爺,您這是打哪里來啊,前面有匪人?傷成這樣?
我盯著那老者的臉上的神情,那疑惑不似作假,便答道:前山剿匪,已盡數(shù)斬殺緝拿,在下趁夜趕往兵營通報,爾等莫慌。
老者連連點頭,我用刀指指篝火上架著的鍋羹:勻些吃食。
老者連忙去取碗筷,我收起刀,沉沉地坐在篝火旁,實在太累,傷口疼的厲害,歇一歇吧,那鍋里不知在煮什么,香氣撲鼻,吃點東西再上路。
那婦人盛了熱羹遞與我,一天未進顆米,雖然只是燴菜,卻格外美味。吃第二碗的時候,身上有了些暖意,我提起精神和那老者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眼光順著四人依次掃過去。
老者農(nóng)人打扮,自稱是花匠,沉默的男人是他兒子,婦人和小姑娘是兒媳和孫女,他們要前往州府的某個員外家打理園林。老者呈上他們的通城文牒,我打眼看看,點點頭。夫妻二人低頭細語著,聽不真切,那小姑娘長得頗為好看,此刻倒不怯我了,坐在花匠懷里,眨著眼沖我微笑。
篝火燃得很好很暖,不時發(fā)出木柴噼啪的燒裂聲,我又仔細端詳端詳四人,不再言語,三碗菜羹下肚,身子好受多了,休息得也差不多了,準(zhǔn)備起身趕路。
老者此刻問道:官爺似有傷在身,打不打緊,老頭子我常年打理花花草草,也知道一些療傷的草藥,這里有不少蛇銜草,要不老頭子給官爺包扎一下傷口?
我猶豫了一下,腰傷雖不流血了,但是依然很疼,往前還有不少路要趕,包扎一下自然是好的。
不過嘛,嘿嘿,小老兒,你怕沒安什么好心,要不是后有追兵,依我平日里的脾氣,說不定還陪你玩玩,看看你葫蘆里到底有什么好藥。
不勞老丈費心,當(dāng)兵的打打殺殺,這點傷還好。我起身,從篝火中挑出一根燃木。夜路有火即可,叨擾了,多謝款待,就此別過,幾位路途珍重。
我舉起火把,行個禮,轉(zhuǎn)身,昂頭沿路向上行去,另一只手緊緊握著刀把,提防著有人發(fā)難,快速離去。那四人也未起身,繼續(xù)低語著,身后響起竹笛聲,那孩子又開始吹奏了。我加快腳步,火光之下,順著竹林間的山路,向上越行越遠。直到身后再次被黑暗淹沒,再也看不到篝火的光亮,我稍稍松了口氣。
我冷冷笑著,好個種花的一家人。
那老者一口官話,雖然農(nóng)夫打扮,從頭到鞋絲毫塵土未沾,干干凈凈,一頭銀發(fā),滿臉皺紋,少說也有七八十了,可是腰身挺拔,眼神炯炯,聲音洪亮,更像個練家子,且這年紀(jì)做那小姑娘的曾祖父倒有可能。
男人乃巴蜀之人,說是種田的,卻穿著長袍,自我出現(xiàn),那雙手就隱在寬大衣袖之間,不曾出現(xiàn),怕是一直藏著兵刃。女子的話聽不真切,可一身絲綢,腰帶上系著一個玉玨,這哪里是尋常農(nóng)戶家的媳婦,江南的豪紳閨秀還差不多。二人眉清目秀,火光下照的真切,也就二十出頭上下,怎可能有個八九歲的女兒。
“祖孫四口”舉家要去給大戶人家打理園林,什么大件家什箱子一概未帶,就只有篝火旁的兩個小包裹。我十三歲就開始舔著刀口過日子,腦子夠使,眼睛夠毒。這四個絕非尋常人家,不是同道中人,就是押鏢護送肉票的,不想深夜讓我撞見了。嘿嘿,要不是老子一身官兵打扮,只怕是剛才坐下喝羹就要糟糕,平日里,兩個三個的對付起來倒還罷了,打不過跑就行,只是今日帶著傷,后面還有追兵跟著,實在不宜撕破臉,還好老子機警。
我正思忖間,火光照到不遠處的竹間山路上,趴著一個渾身血跡之人。
我停下腳步,抽刀出鞘,舉高火把環(huán)顧四周,仔細聽聽,除了風(fēng)聲,竹葉聲,前方受傷人的呻吟,不似有其他動靜。我慢慢走過去,用腳將地上之人踢翻過來,那人披頭散發(fā),面目血泥交錯,看不清楚年紀(jì),渾身是血,多處有傷,胳膊被砍斷了,腹部的有刀劍傷,這兩處最為致命,不斷有血涌出。他衣衫襤褸,身上除了血就是泥土葉子,想是受了重傷,從山上某處爬下來的,此刻怕是已經(jīng)神志不清,口中喃喃自語:……不可……你。我蹲下來,貼近過去,也聽不真切,反反復(fù)復(fù)也就這些內(nèi)容。
這人多半就是花匠一家人所傷了,果然不是什么善類,我起身邁步,那重傷之人卻用僅剩的手,緊抓住我的褲腳不肯松開,他盯著我,渾身抖得像個篩子,絮絮叨叨的說:……你……你。
我一腳踢開他的手,繼續(xù)向前,走了兩步,我折返回來。
我俯下身,一刀深深插進那人胸口,他不停咳嗽,血從口中不斷流出,我笑著說:兄弟,原本你我也無仇怨,不過你穿著官靴,而我是個賊,雖說官賊不兩立,看你這么難過,我今日送你一程,你可要記得我的好。
他盯著我,似是還要講什么,可是只是不停咳血,火光之下,那雙眼睛很快黯淡下來,身子也無動靜,我抽刀出來,這算是死透了。道上出現(xiàn)這么一具尸首,應(yīng)該也能耽擱一下追兵的時間。
我加快步伐前行,竹林里曲曲轉(zhuǎn)轉(zhuǎn)行了片刻,遠方高處又有點點光亮透出,越走越近,我愈發(fā)疑惑,篝火的光亮,隨風(fēng)而來的笛聲,我是迷路了,怎么又繞回來了?
果不其然,我又回到了剛才那花匠一家歇腳之處,他們四人也頗為意外。我舉著火把,前后走了走,勘察一番,我所行之路,分明是一條上山道,一路也是順山勢而上,我在山中多年,這點不會有錯,怎么會又繞了回來?除非……我看著他們,心中驚疑未定,目光掃向篝火之上的鍋羹,這菜羹里怕是下了迷藥,不然怎會讓我失了方向。
我心中思索,這當(dāng)口那花匠起身作揖道:官爺怎么又回……,不待他說完,我抽刀橫劈,老者慘聲倒地,我飛身躍起,跨過篝火,揮刀凌空向下,將藏手袖中的漢子砍翻,一把揪住那婦人頭發(fā),抓到身邊,一刀插進心口。
我慢慢將刀拔出,血噴漿出來,那婦人無聲無息地癱軟下去,眼前的小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嚇傻了,臉上竟然還掛著笑。
此刻,林中深處忽的跳出一個人來,擋在我和小姑娘之間,揮刀向我而來,嘴里大喊不可傷人。原來還藏著一個人,我招架了一下,那人刀力軟綿,我放心下來,使出全力,將刀快速舞起,水潑不進,對方招架不住,先是被我砍掉了發(fā)箍,他刀勢慌亂,我瞅個破綻,狠狠一刀砍在他左臂之上,那人慘叫倒地,大喊一聲,脫手將刀向我全力擲出,我出刀格擋,側(cè)身躲開,他已起身,抓起那小姑娘鉆入竹林之中。我起身追趕,腰間傷口卻在此刻再次崩裂,疼痛難忍,我伸手入甲,滿手的血。
我舉起火把,竹林深處太過黑暗,我獨自如此追擊,恐遭暗算,身后有些響動,我轉(zhuǎn)頭看去,那花匠還未死透,掙扎著向竹林爬去。我走過去,一腳踏住他的脊背,狠狠踩住,老者哀嚎起來:官爺官爺,為何要傷我等啊?
我啐了一口,冷笑道,呸,事到如今,還在演戲,你若是花匠,我便是圣人了,說,你們到底是何人,為何在此安排老子!那老者不住哭喊,一再重復(fù)之前的身份。我問的煩躁,最后說道,也叫你死個明白,老子才不是什么官爺,老子是這山里的大王,要不是官兵來壞我自在,豈能讓你等輕易入山!
結(jié)果了老兒的性命,我仔細勘察左右,除了兩個包裹,就近無其他物件,包裹里也只有干糧火石,以及花草種子,值錢東西,看來是在附近什么地方藏著了,由剛才那個同伙看管著。那男人倒不是藏手袖中,原來他失了雙手,是個殘廢,倒讓我意外。我扯下婦人腰間的玉佩,這個值不少銀兩。我看看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多少有些可惜,要不是這光景非常,一定好好享受一下。
我用水囊里的水洗了洗臉,清清神氣,滅了篝火。仔細辨辨山勢,向上走去,剛才這一番折騰,傷口又開始流血了,手里的火把也棄了,他們還有同伙在竹林之中,我不想在山路上當(dāng)活靶子。
依舊無月無光地行了半個時辰,遠方高處點點光亮透出,風(fēng)中又傳來竹笛的聲音,我一身冷汗,這次無疑是向上走的,那四人死的死,逃的逃,怎么又出現(xiàn)這般相似景象?
莫不是,鬼打墻?
山中住的久了,總有奇譚怪志,我倒是從未遇到過,也不去多想,干得是殺人越貨的營生,要是信了,刀會不穩(wěn)。
笛聲隨風(fēng)傳來,之前未曾留意,現(xiàn)下聽了,曲調(diào)悲戚,只覺說不出的詭異。顧不了這許多,管他是人是鬼,老子今天也要會一會。壯壯膽色,我握著刀向光亮處行去,不多時看到那堆熟悉的篝火。
花匠祖孫四人,圍著火依次坐著,神色姿態(tài)如初,身上毫發(fā)未傷,仿佛上一場殺戮從未發(fā)生,小姑娘停了笛聲,四人望著我,這一次少了驚異之色,似乎我的出現(xiàn)并不意外。老花匠笑著拱手:官爺,又見了。
我心內(nèi)驚疑未定,舉刀指向他們:老匹夫,你們是何方妖孽,為何為難與我?有何仇怨,有何所圖,不妨直說。
這倒奇怪了,老花匠不緊不慢地說,天色已晚,我們一行在此休憩,還與官爺行了方便,剛才動手殺人的分明是你,怎么成了我們?yōu)殡y官爺了。
要是鬼怪妖人,何必和我如此兜圈子,我怕早已亡了。我尋思著,此刻怕不是幻術(shù)?剛才他們的血還在兵甲上未干,該死的早就死了,我砍的真切,如何能復(fù)活回來。
原來如此,我心下明了,那老花匠拱拱手,正要說什么,不待他開口,我轉(zhuǎn)身回頭,一個箭步來的那小姑娘身邊,一刀劈下,那孩子應(yīng)聲倒地,身子連同竹笛一起,變成兩半。
四人當(dāng)中,剛才逃走的只有她,要操縱幻術(shù),只可能是她或是那個藏身竹林的人,先除了她再說。
老花匠嘆了口氣:官爺真是……。我提刀向他而去,這三人尚存,說明幻術(shù)未破,藏身那人遲早現(xiàn)身。
忽然身后有風(fēng),我一直提防,俯身避過這一刀,扭身揮刀,和身后那人戰(zhàn)到一處。一兩個回合之后,這藏身之人已不像剛才時綿軟,火光下定睛一看,這人著兵甲,持官刀,長得竟和我一模一樣!
我心下驚異,一刀架開,向后跳出幾步,問道:你是何人,竟扮做我的樣子?那人絲毫未停,揮刀逼近,刺中我的大腿,我下身吃疼,趕忙格擋開來。
這狗賊,竟用幻術(shù)擾我心智,我一邊和那人斗勇,一邊想著,剛才藏身之人分明羸弱,眼前這個自己卻勢均力敵,莫非,我在與幻象相斗,而他裝成其他三人模樣,在旁操縱?
想到此處,我側(cè)眼掃去,那三人在原地未動,饒有興致的看著我二人纏斗,我心意已定,架開一刀,急速躍至老者身邊,揮刀劈翻,順勢一個打滾,橫刀而出,再砍,那夫妻二人隨刀而倒,身后有人追來,我扭身,終究分神慢了片刻,被那人刺進兵甲,刀入后背,再深入就到后心,我借力前傾,倒在篝火旁,逃過一劫,但這背傷可不輕,轉(zhuǎn)身過來,來不及爬起,那個自己一步步逼過來。
怎么回事?要是幻術(shù),這人應(yīng)該已經(jīng)散了,難道他就是剛才藏身之人?這誤判差點要了我的命,此刻我已陷入劣勢,那人揮刀而下,來不及多想,我揮刀將身旁篝火挑起,火星在那人刀上四濺,星星點點蹦進他眼中,他大喊一聲,用手捂眼,刀勢不由緩了,步子也亂了。
我滾到他身下,一刀捅出,于兵甲縫隙處刺進他的小肚。那人慘叫一聲,我爬起身,揮刀連砍,他亂了陣腳,只能招架,就要得手之際,背上刀傷發(fā)疼,最后一刀還是軟了,竟然砍偏。
還好那人眼中吃疼,腹部有傷,揮舞官刀,身形不穩(wěn),一腳踩空,順著下山路滾入竹林。
我待要去追,可此刻新傷舊痛,流血不止,力氣快用完了,且這人也是個扎手的,潛在竹林里勝負未知,不如早早離去。
我查看一番,花匠和夫妻二人與此前尸首無異,那小姑娘身上卻是藏了一把匕首,而且這匕首,竟然是我的。入夜之前與官兵纏斗換衣時遺失了,此刻為何出現(xiàn)在她身上。
我收起匕首,辨了辨山勢,以刀為杖,棄道而行,走入竹林,登高而去,這正路上怕是被人施了什么妖邪,如此,不如入林開路,翻過山去。行進當(dāng)中,不時回頭望去,眼見腳下那團篝火還在燃著,只是離我越來越遠,直到看不見了,我稍稍心安,那黑暗之中,似乎終于肉眼可見山頂了。
竹林中摸索著再行,一低頭,不知不覺中,又走到林間正路里來了,內(nèi)心有感,我抬頭,遠方高處,星星點點的火光透出,隨風(fēng)而來竹笛的悲戚之音。
我又慌又亂,不敢再行,坐下來思忖,若深入林中,看今晚的情形,不管走哪里走多深走多高,怕還是會回到那篝火旁,在此處等天明么?就算追兵趕不上,身子這個情況再拖下去怕是要有性命之憂。既然著了道,逃不了,不如干脆低頭認栽,虛與委蛇,靜待其變。
心意已定,我收了刀,慢慢向那光亮處行去,現(xiàn)在聽來,風(fēng)里的笛聲仿佛是招魂的一般,生死有命,伺機而動吧。
果然,一樣的篝火,一樣的人。老花匠一家人靜靜圍坐在篝火旁,好似等著我一般。
我撲通跪倒在地,爬到花匠身旁:小的有眼無珠,亡命自保,竟然冒犯了幾位高人,還請贖罪,饒小的一條狗命。
四人忍不住笑了起來,那花匠看著我道:官爺何出此言,我們不過尋常百姓,您可是這山里的大王。
我趕忙俯下頭:不不不,小的該死,小的胡言亂語,不知天高地厚。
老花匠對著家人們問道:你們說這官爺此刻為何如此啊?
婦人抿嘴莞爾:大人發(fā)現(xiàn)自己走不出山,心中著急啦。
男人笑道:大人發(fā)現(xiàn)殺不了我們,于是要低頭打探打探,摸摸咱們祖孫的底。
小姑娘笑的像銀鈴一般:等大王哥哥搞清楚怎么出去了,一定手起刀落,殺了你我。
背上冷汗冒出,傷口更疼了,我急忙連連磕頭說道:哪有此等思量,小的該死,小的不敢。
直到頭磕破了,才聽到老花匠緩緩說道:官爺不必如此,你這套把戲我們也不是第一次見了,早看累了。
婦人抿嘴莞爾:上個大人不但磕頭了,還痛哭流涕呢。
男人笑道:上上上個大人倒是沒磕頭,只是切了自己的小指,以示悔過呢。
小姑娘笑的像銀鈴一般:還有把自己脫光了,用火棍抽自己的大王哥哥呢。
我只聽得一頭霧水,不明就里,看這意思,我竟來過數(shù)次?為何毫無印象?我對四人行了三個大禮:小的不過螻蟻一般的賤命,要殺要剮,任憑諸位高人處置,只是恕小的愚鈍,在下今夜這是第四次碰見高人們,實在不知所說之事,也不知之前是何事沖撞了幾位,才落這般境遇,還請高人明示。
四人沉默不語,只是盯著篝火,火焰燃得正旺,不時發(fā)出噼啪聲。良久,老花匠開了口:官爺,既如此,不妨講明,老兒我確確實實是個花匠,只是尋常花草不太種的。無先生與常先生在官爺身上打了個小賭,老兒我要還他們?nèi)饲椋谏缴舷铝算曃采卟荩€局未明之前,這山,官爺翻不過去。
無先生?常先生?我心下迷惑,未曾聽過,難道是之前的仇家前來尋仇?我遲疑道:卻不知打了什么賭?
官爺?shù)臍I(yè)太重,故有此劫。兩位先生賭官爺何時能自己破了這循環(huán)往復(fù)的局,常先生賭壹萬捌仟次,無先生賭官爺永生不破,終困于此。這賭局眼下正是第三千六百七十回。
老花匠見我面色有疑,淡然道:官爺要是不信,大可將我四人殺了綁了繼續(xù)上路,看看會不會有何變化。
聽著情形,依之前情景,老頭說的大半是真的,我心中暗惱,這兩個所謂的先生當(dāng)真過分,如此戲耍于我,待過了此劫,定要數(shù)倍償還。
我不動聲色,依然畢恭畢敬地請教:賭局既是法術(shù)奇能所設(shè),那必有應(yīng)對破局的法子,小的愚鈍,粗鄙莽夫,求幾位高人神仙恕在下不知冒犯之罪,所為只為謀生,還望垂憐指點一二。言畢,我起身對著四人三跪九叩。
老花匠面有為難:破解之法不是沒有,只是官爺這情形……嗯,不好說,不可言。
我聽下大喜,連連磕頭:還請老仙人賜教,在下感激不盡,破局出山之后,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老者將我扶起,嘆道:老頭子在這局里陪著官爺一遍一遍的折騰,待得確實有些倦了,可是受人之請,所托未盡,豈能又輕易將這局破了?怕是要官爺自己好生琢磨。
我正要再求,另外三人分別接話。
婦人抿嘴莞爾:說不定大人將這竹林燒了,滿山樹木連同什么設(shè)局的勞什子草一并化為灰燼,就出山去啦。
男人笑道:不妥不妥,大人既要重新做人,就得效法苦行僧,廢了功夫,自己在此靜待投官,任由衙門處置。
小姑娘笑的像銀鈴一般:你們說的都不對,爺爺剛才都說了,大王哥哥殺業(yè)太重,他要回去消了才成,之前的消不了,至少今夜的,他說不定回頭阻止,才能破局。
這三人說完,忽然一起大笑,齊聲說:大人也可將我等殺了,多殺幾次,就出山啦。
我左右疑惑,殺這祖孫四人,必是不可能破局的,看來逃出之法就在這三人所說里,只是誰說的才是真的呢?我不由望向老花匠。
老頭嘆了口氣:官爺當(dāng)真認不出他們?nèi)耍空J出來,說不定你就明白怎么出去了。老丈只能言于此了。
這是什么意思?我依次看過去,這一家三口,分明是今夜初見,我如何能認出來?我仔細思量,卻還是想不起來。
就在此時,我留意到,那小姑娘手持的短笛不知何時變成了一把匕首,火光下看的分明,正是我遺失的那把。我摸了摸腰帶,剛才在上一個她尸首上搜出來的匕首已經(jīng)不見了。
莫非,她說的才是對的,我要回到之前的竹林,去阻止今晚的殺業(yè)?
等等,我猶豫間忽然想起,那藏身竹林的第五個人呢?話已經(jīng)說開了,既然未在此處現(xiàn)身,那他就不是設(shè)局之人,那是誰呢?我頓悟:是上一個循環(huán)局中的自己。難怪在上個竹林中與我纏斗良久,那并不是個幻術(shù)。
如此說來,小姑娘說的才是破局正解,不然上個我回去干什么?婦人說燒山,怕最后燒的還是自己,漢子說自傷自首,那我還翻山作甚,他說的分明也是死路。
這三人我都不相識,老者卻提醒我“認出來”,多半指的就是我的匕首,必是如此!
多謝老丈!多謝三位高人!我高聲道,再拜起身:在下這就破局去,待出山他日相見,必當(dāng)報恩!老花匠和夫妻二人不再言語,只是看著篝火發(fā)呆,只有那小姑娘沖我眨了眨眼。
我轉(zhuǎn)身下山而去,確實,等老子真的翻了山,一定找你等和那兩位先生好好報恩。
沿著林間路下山,先隱隱聽見笛聲,接著便看到了那堆篝火。我加快步伐,細細思量著,剛才自己與另個我纏斗時,是用篝火取勝,想必待會見到的我還是會用這招,一定小心提防。
篝火越來越近,我棄道入林,摸將過去,身上有兩處傷不輕,還要趁其不備,快戰(zhàn)快決,制住另個自己,省的他再殺人,才好破這局。
待從林中深處靠近篝火,正看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我”舉刀叫罵:……有何仇怨,有何所圖,不妨直說!
糟糕,有些晚了!我快速從林中跳出,那個自己卻已經(jīng)跳近前去,將那小姑娘劈成兩半。我心下惱怒,抽刀向他砍去,兩人戰(zhàn)做一處,小女孩已死,這次怕是不成了,只能快點料理了他,趕到下個我動手的地方。
斗了片刻,這個人認出我來,驚疑質(zhì)問,我正等此刻,并不答話,一刀刺出,戳中他的大腿,我心中清楚,小姑娘既死,我倒不必護著老花匠和夫妻,只等對面這個自己前去砍人再次露出破綻。
片刻,他身形慢慢向那三人移去,我假意不知,隨他步伐,蓄勢待發(fā),等他露背給我。果不其然,他如我之前一般,先殺花匠,又砍夫妻,我就等這一刻,一刀狠狠刺進他背里,他吃疼倒地,我急步跟上,佯裝揮刀,其實卻防著他挑起篝火。
沒成想,走的太急,竟然被什么東西差點絆倒,就在此刻,那個地上的自己一個翻滾過來,一刀刺進我的小腹。
疼痛難忍,我大叫,一刀砍向身下的自己,他抽刀格擋,爬了起來,與我再戰(zhàn)。
受此一刀,我的身形已然穩(wěn)不下來,之前不顧舊傷聚的那口氣散了,他卻越戰(zhàn)越勇,片刻間,我又中數(shù)刀,毫無疑問,已經(jīng)殺不了他了,血越流越快,越斗越覺得頭暈?zāi)垦#荒_踩空,我從山道上翻滾下來,跌入林中。
如此向山下翻滾了許久,抓住一塊山石,方才停住。只覺得骨頭架都要散了,失血太多,頭暈?zāi)垦#滹L(fēng)吹過,只覺得渾身上下正有千百個透明窟窿,穿風(fēng)割裂,透心疼。身上沉重,我脫去偷來的兵甲,輕松不少。緩上一緩,把衣衫撕開,大致包扎一下,勉強可以行路了。
為何如此啊?想來是不知被誰的尸首絆倒,才出現(xiàn)那個大破綻。莫非是那夫妻二人從中搗亂。我思量片刻,路數(shù)怕是對了,身體傷成這樣,和其他的自己硬碰硬怕是不行了,要找那個小姑娘問問,除了殺了之前的自己,還有阻止這循環(huán)殺伐的辦法沒有。
我以刀為杖,掙扎著起身,向山下摸索而去,已經(jīng)能聽得到笛聲了,篝火也不遠了。
半走半爬的摸到跟前,已經(jīng)晚了,“我”已砍到了花匠和夫妻,正拿著刀逼近小姑娘。
不可傷人!我大叫一聲,從林中跳將出來,擋住一刀,護在小姑娘身前。此時我根本無力與之前的自己相斗,先是發(fā)箍被削,不多時,胳膊又中了一刀,差點被砍斷,使全力將刀扔出,我轉(zhuǎn)身抓著小姑娘的手,鉆入黑暗的竹林之中。
在竹林中逃了片刻,我實在無力,料想那個自己不會追來,于是停下來,松開小姑娘的手,我問道:小姑娘,你沒事吧。
小姑娘哆哆嗦嗦,一臉驚恐地說:多謝這位公子相救。
是我啊,小妹妹,不,小仙女。我想起自己此刻披頭散發(fā),用沒受傷的手撥了撥頭發(fā),湊近過去:多謝之前的指點。
那小姑娘眨眼間換了個人一般,神色不再畏懼,輕輕笑道:原來是大王哥哥啊。
我苦笑道:仙人明鑒,依您的指點,來阻殺業(yè),沒成想?yún)s淪落如此。眼下硬去阻那殺局怕是多有不便,該如何破局,還望您示下。
小姑娘牽起我尚好之手,輕道:大王哥哥莫慌,隨我來,我?guī)闳テ凭值恼贰?/p>
我任小姑娘領(lǐng)著在林間慢慢穿行,身上傷勢過重,再走下去難免不妥,想要停下來歇息,可不知怎的,她牽手的時候有種熟悉之感,我漸漸安心下來,料想那破局之道即將就在眼前。
大王哥哥,行走之間,小姑娘輕聲笑道,二十年前,我也是這般牽著你的手呢,那時你真是年輕俊朗呢。
二十年前?我正要追憶,只見黑暗之中,出現(xiàn)了星星點點的綠光,風(fēng)中有野獸低沉嘶吼,飄來腥臭之氣。
遇到狼了。
小姑娘嚇得叫了一聲,躲到我身后,我心中略慌,這怕是被我這一路的血吸引過來了,我想到那把匕首,正待開口,只覺剛剛受傷的左臂一涼,那條將斷未斷的胳膊被削了下來,血噴濺出來,我疼的大喊,身上背上不知又被扎了幾刀,跌倒在地。
那小姑娘拾起地上我的斷臂,丟向狼群,黑暗里響起一片咀嚼嘶吼之聲。她輕輕哼著曲,揮著手中的匕首,那匕首的光澤像螢火蟲一般,輕盈的舞著。
我躺在地上,疼的扭曲起來,我恨恨地盯著她。
她笑嘻嘻地眨眨眼,大王哥哥,你好嚇人啊,別意外啊,我只是不想被你送到狼口之中。
她頓了一頓,輕輕說道,像我爹爹一樣。
一瞬間,我的記憶被打開,我認出了她,只是怎么可能?
小姑娘蹲下來,看著我,輕輕笑著說:不錯不錯,是我。那一年冬天世道不太平,又打仗又鬧災(zāi)的,大家都快餓死了。我聽了你的花言巧語苦苦哀求,求爹爹把你從死人堆里背回山里,僅有的口糧分給你。
身上的傷再不醫(yī)治怕是要死,我想出聲哀求,剛一開口,小姑娘一腳踩住我的右臂,一腳踏上我的胸口,捏開我的嘴,在口中一陣亂攪。我發(fā)出殺豬一般的嚎叫。
她啐了一口唾沫在我臉上,在旁邊坐下,她又笑了:你這張嘴這些年謊話連篇,聽得我實在是煩躁。再發(fā)聲,我就把你身上的肉一點一點割下來,就像你當(dāng)年害我一般。
黑暗里陷入安靜,她繼續(xù)自言自語:我那時還小啊,不明白,到死也不明白。三九天,大雪,我們一起外出尋食遇到狼群,你為了保命,竟然傷了我爹爹留給狼群。后來斷糧幾天,你終于還是忍不住,把我也烹了吃,就用這把匕首。我死的時候,傷心啊難過啊,不過更多的是不明白,人為什么能如此?所以啊,我的怨念太重啦,就附到這把匕首上了,一直跟著你整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嘿嘿嘿,看著你殺了那么多人,害了那么多人。
后來我明白啦,你不是人,連強盜也不配,你不過是個無心無肺豬狗不如的獸,頂了一張好看又良善的臉。這張臉,我也看得倦了,真是惡心透了。
小姑娘伸手過來,在我臉上一陣切砍,皮開肉綻。她舒了口氣,笑盈盈地繼續(xù)說:這樣好多了。
我想報仇,可是我就是個魂啊是個小鬼啊,怎么辦啊,于是我等啊等啊,直到今天晚上。小姑娘大笑起來,笑的喘不過氣。
大王哥哥,你是不是以為你還活著,你只是困到這局里了?你摸摸后腰。我依言摸去,最早那個腰傷處赫然插著一把匕首,我想拔出來,可是手上無力,怎么也拔不出來。
你傷了官兵,想偷人衣甲,趁黑出逃,可惜換衣時把我掉落在那官爺手邊,官爺命大未死,在你穿甲時一刀結(jié)果了你,想起來沒有?
我直聽得肝膽俱裂,胡說胡說,可是舌頭爛了,卻發(fā)不出一個整詞。
小姑娘很滿意我的反應(yīng),她繼續(xù)微笑著,像一朵花一樣:我最懂大王哥哥啦,我都和花匠爺爺還有他們講了,咱們大王哥哥啊,極惡之人,改是改不了的,悟是悟不到的。可惜啊殘廢的官哥哥太直,漂亮的貴氣姐姐太善,要不當(dāng)年怎么被你騙了殺了辱了燒了?你呀,就是個畜生,既然如此,這銜尾蛇草造的地獄最適合你了,你這樣的魂魄,先在這里一遍一遍受該受的,消該消的業(yè)吧。
無先生都說啦,你這么愛殺人,就在這里讓你殺個夠,常先生也沒意見,這才找來的花匠爺爺。誒,你往哪兒爬啊,還有更精彩的沒聽完呢?你是不是以為,那個賭是賭你的?錯啦錯啦,他們是在賭我,我怨念太深啦,要投胎做人還要消了這份執(zhí)念,什么時候能消啊?常先生賭我騙你殺你壹萬捌仟次,無先生啊,他賭我永遠要這么騙你殺你下去。
小姑娘停了停,你說,他們誰會贏啊。
我用一只手拼命爬著,這一定還是這局里的陷阱障眼法,一定可以破的,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身后傳來小姑娘的笑聲,我不敢回頭,只是向竹林深處爬著,小姑娘哼起曲子,悲戚低沉,頃刻后發(fā)出銀鈴一樣的笑聲。
痛快痛快,你爬的真好看,你要快些哦,待會我就帶著匕首和狼兒們?nèi)プ纺憷玻灰姴簧 ?/p>
那聲音噶然而止,我使出全力向前,泥石草葉此刻如刀一般,我覺得渾身力氣就要沒了,可是不能停啊,至少告訴下個自己今晚的事情。我昏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正趴在竹林間上山路上。
遠處,一個我正執(zhí)著火把,持刀一步一步走過來。
(P.S 致敬恐怖游輪的一篇習(xí)作)
[責(zé)任編輯:linlin]
相關(guān)文章
- 1 國家藥品集中采購倒逼藥企殺價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泡在實驗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用車廂 到底有無必要?
- 10 教練長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實名舉報
- 1 國家藥品集中采購倒逼藥企殺價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泡在實驗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用車廂 到底有無必要?
- 10 教練長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實名舉報
- 房地產(chǎn)業(yè)或迎融資"緊箍咒" 多家房企積極表態(tài)
-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密集發(fā)布
-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
- 中央軍委訓(xùn)練管理部四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著裝辦法》退役軍人可以在公開場合穿軍裝了
-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泡在實驗室
-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85歲老黨員不顧危險跳水施救82歲落水老太
-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方致輕傷被判刑
- 六大關(guān)鍵詞讓你了解蘋果新品發(fā)布會
- 加密貨幣轉(zhuǎn)正!多米尼克立法確認波場系代幣為國家法幣
- 蘋果今天發(fā)布了 Safari 技術(shù)預(yù)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fā)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fā)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zhàn),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zhì)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tài)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fā)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huán)球觀天下
- 高等數(shù)學(xué)(上)習(xí)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jīng)大學(xué)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zhuǎn)函數(shù)-當(dāng)前要聞
- 鄉(xiāng)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nóng)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jié)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fā)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yǎng)豐富哦~
- 金秋時節(jié)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dāng)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yīng)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huán)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nèi)容大變買個ip網(wǎng)劇套原創(chuàng)劇利用書粉基礎(chǔ)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yǎng)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yù)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huán)球新資訊
- 養(yǎng)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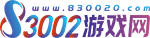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