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說個(gè)事。”
“你說。”
寒氣貼著半敞的玻璃縫隙爭(zhēng)先撲入,行車舊道,南國的冬日遠(yuǎn)遠(yuǎn)比不上北方這般直爽與嚴(yán)厲,但所幸今年我已較于以往更早地逃離。她在駕駛座上掌控著回家的速度,而我則是凝神望向窗外,心緒之門砉然而啟,沖出隧道的剎那,呼嘯聲將所有處于靜默中的夢(mèng)與魂靈撞得粉碎,又猶如黝黑的潮水鋪天蓋地湮沒海岸邊浮游的庸碌。
山野闊蕩,躁動(dòng)不安的短暫的生命好似廢棄排水渠底的荒草。
“你大姑夫十二月的時(shí)候去世了。”
“嗯。”
對(duì)于這個(gè)消息,我其實(shí)并不意外;而對(duì)于我不驚不怪的態(tài)度,她也沒有表現(xiàn)出多余的情緒,就仿佛打水漂一樣,剛剛只是起了個(gè)頭,真正的漣漪永遠(yuǎn)潛伏于深不可測(cè)的下一步。
暑假時(shí),我就從家人躲躲閃閃的只言片語中捕捉到他們所刻意隱藏的悲傷與災(zāi)難,“醫(yī)生讓他能吃的話就多吃點(diǎn)想吃的”,“腦袋里長了個(gè)瘤子,查出來已經(jīng)晚了”,隨后父親母親還曾陪著姑姑與表哥來我家附近的山上看墓地,那些小時(shí)候常常在電視劇中不以為然的情節(jié)突然間從角落殺來,奪框而出,然而落座觀眾席的我們卻無力左右。
劇烈的震蕩,每半年的歸鄉(xiāng)頻率讓這個(gè)本就愚鈍的孩子關(guān)于親情的感切出現(xiàn)了斷層,而隨著年歲增長,震蕩的次數(shù)只增不減。
以及我姥爺。
此時(shí)此刻,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全然錯(cuò)過了所有那些已逝親人們的葬禮,深夜時(shí)分偷偷地哭著,泣不成聲,又不想麻煩他人費(fèi)神安慰。
“再跟你說個(gè)事。”
“你說。”
“你爸還在家里,在你爺爺奶奶家,明天我們?nèi)ソ铀!?/p>
“我爸——他竟然還在家?”我驚叫出聲,因?yàn)槠綍r(shí)這個(gè)時(shí)候他只應(yīng)當(dāng)還在遙遠(yuǎn)的新疆的礦廠工作,而后我自以為是因?yàn)楣酶冈岫Y他回來辦事。
“你爸十二月的時(shí)候做了個(gè)手術(shù)。”
“什么手術(shù)?”
“有個(gè)瘤子。”
霎時(shí),不知道是心靈還是哪處看不見又不知名的地方,支撐著理智與情感的巨柱轟然崩塌,悄無聲息。晴天之上高懸的冬陽令人頭暈?zāi)垦#熊囷w速突進(jìn),薄情拋下百千高低起落的灰禿山丘,天寒地凍。
但下一秒,一如往常那般,她以那種糅雜了悲喜、遺憾、平靜、勇氣、錯(cuò)過與堅(jiān)韌等能量的姿勢(shì),奮力揮臂,交疊,旋轉(zhuǎn),緊接著打破魔咒,救起了即刻幻滅于地平線盡頭的火團(tuán),再次將我拉入生命的溫暖。
她坐在純白色山航經(jīng)濟(jì)艙臨近機(jī)尾的中間座椅里,這一切都是如此新奇,九月份的天氣延續(xù)了長夏的暑熱,而舷窗隔斷了濟(jì)南郊外那浮亂躁動(dòng)的短風(fēng)。
抬眼望向舷窗外那片愈來愈遠(yuǎn)的鄉(xiāng)土大地,驀然間有種仿佛心悸般的下墜感。四十三歲的她第一次坐飛機(jī),傻孩子不清楚當(dāng)時(shí)的她究竟是懷著怎樣的心情送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去偏遠(yuǎn)南國小島讀大學(xué),她定是在笑吧——那扭過的臉龐上的表情,傻孩子先是如此堅(jiān)信著,隨后也開始了懷疑。
“她終于解放了。”某個(gè)悄聲融冰的深夜,傻孩子在微弱臺(tái)燈下寫完這句無處安放的話,也許跨越瓊州海峽、于兩千四百多公里外的家鄉(xiāng),鈷藍(lán)色的夜空依舊是望不見任何星辰,她正摟著兩只一大一小的貓咪安然睡下,夢(mèng)中依舊盡是熱愛的人物與故事,睡夢(mèng)外依舊是滴答滴答從容不迫走過的時(shí)間。
命運(yùn)容不得別人對(duì)它開玩笑,但它又總似頑童般捉弄著每個(gè)人。
高三時(shí),傻孩子經(jīng)常同她打趣,父親常年漂泊于大西北,他的背影早已被滿天黃沙所掩埋得銹跡斑斑,那個(gè)男人的背影襯著逐漸衰弱的燭火被無限地拉長,最終延展成一座橋,一座窄窄的、單向的、歲月斑駁的獨(dú)木橋。
每每談到志愿填報(bào),傻孩子笑自己可能會(huì)去南端浪跡天涯海角,就像自己的父親那般,追著祖國的邊緣成長;她回道權(quán)當(dāng)是支持祖國發(fā)展做的家庭貢獻(xiàn),隨之而去,安之而來,未來的事情誰也說不準(zhǔn)。
來年,傻孩子問她想不想看海潮澎湃,問她想不想看鳳凰花開,問她想不想看騎樓莓苔,問她后悔不后悔當(dāng)初的選擇與等待,只因未有人曾料到結(jié)果還真就應(yīng)了當(dāng)年的無端戲謔。
“等你上大學(xué)了,她也就解放啦。”這是那段日子里長輩們對(duì)傻孩子說過的最多的一句話。
她解放了嗎?
對(duì)一個(gè)吃苦了半輩子的婦女來說,什么是解放?
是住上漂亮寬敞的大房子嗎?是開上闊氣舒適的小洋車嗎?是孩子事業(yè)有成、家庭美滿嗎?哪樣才算得上她的解放而不是旁人眼中的解放?
亦或者她仍然拒絕對(duì)生活唯唯諾諾,絕不容許蟄伏于地表深處下的那些蠕蟲劣豸糟蹋自己的生命,也絕不容許自己的家人被厄運(yùn)剝離于自己的身旁,她保持一貫的作風(fēng),充滿生命力地追求著少女時(shí)期的夢(mèng),追求著獨(dú)具眼光的美學(xué)。
就仿佛自己從未老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她出生了,山東東營鹽堿地并不會(huì)給予莊稼太多肥沃的幸福,記憶里最深刻的是棉花與照料農(nóng)田里的棉花,誰會(huì)想到這片貧瘠困頓的土壤在十幾年、二十年后會(huì)孕育出嶄新的富裕,所以她同其他人一樣,想著早早逃離,遠(yuǎn)遠(yuǎn)逃離,就恰逢踩著那個(gè)異常敏感的時(shí)代的尾巴。
而后的十月,斬破濃霧,烈陽怒放,如火將燃,倍感陌生的民眾們唱啊唱,迷惘的歌聲響自荒原,前所未聞的歌聲響自干裂的指尖,溫煦的歌聲響自天南地北。
兩年后,又是人們熟知的改革開放。這是一段對(duì)于尋常筆墨來說連寫意都異常艱難的故事,或許它不知何時(shí)已經(jīng)丟失了內(nèi)核,余下的果肉繼而腐化為肥料,只有當(dāng)不計(jì)其數(shù)的青苗兀自破土而出、拔地而起的壯景被廣而知曉時(shí),他們才會(huì)明白那些種子就是之前以為被丟失的內(nèi)核,誕生出了千紅萬紫。
清晨的平房學(xué)校門口,野孩子蹲在草叢邊緣順著教室的方向失神恍惚望去,冬天取暖用的爐子被擠在墻角。她大約十三四歲,穿著件比她體型要大很多的粗布外套,就仿佛有個(gè)笨重的肥麻袋罩住了,鼻子、臉頰和雙手被凍得紅腫且毛糙。燈都是定點(diǎn)照明的,直到她上高中,早晚自習(xí)也還都是用蠟燭來偷點(diǎn)光亮,晨讀望去,鬼火一片。
她不知道幾點(diǎn)了,路上沒有什么行人,她孤零零地杵在原地,盼望著太陽快快升起,依稀的駭人犬吠聲從遠(yuǎn)處傳來。
學(xué)校附近靜悄悄的,野孩子感到很不自在,難過,又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只得捻著泥里的草蒂在地上畫著不知所以的圖案,而后再扯一把狗尾巴草編著兔子和小太陽。
剛醒來時(shí)她以為自己要上學(xué)遲到了,爬起來拖著那雙沉甸甸的鞋就向?qū)W校跑去,隨后野孩子才發(fā)現(xiàn)自己來得太早、學(xué)校都還沒有開門。
事實(shí)上,對(duì)于那些年家里沒有時(shí)鐘的野孩子來說,提早到校是常有的事情。怕遲到、但又不知道時(shí)間,她只得認(rèn)每天摸黑爬起來,尤其是冷冬時(shí)。
她對(duì)于過去的敘述平淡而冷靜,傻孩子也難以想象甚至難以將那些墜落到湖底四五十年的影像完好無損地打撈起來。但傻孩子的目的本就是她,自己難以清晰地了解那個(gè)時(shí)代,陌生揭開面紗后依舊是陌生,自己只能順著她曾經(jīng)活過的脈絡(luò)去細(xì)細(xì)找尋,卑微地祈求可以獲得零星的溫潤。
家里排行老大,底下還分別有個(gè)弟弟妹妹,所以她學(xué)習(xí)很是爭(zhēng)氣,高中去了縣里一中。
“等一等,咱們學(xué)校有幾個(gè)名額可以保送山大的,以你的條件,我認(rèn)為你可以試試。”班主任向她說明了情況,“你喜歡文學(xué),有保送名額的這兩個(gè)專業(yè)和文學(xué)也很類似啊,哲學(xué)和考古,雖然不怎么適合小姑娘,但我相信以你的性格肯定能沉下心來的。”
她的嘴唇在發(fā)抖,這是老師第二次問她的選擇,這事已經(jīng)臨近截止日期了。
凝視著窗外的家槐,她似乎在鼓足勇氣與力量去長大為成年人,家里的長輩對(duì)于高考這種事情甚至還沒有自己懂得多。
“多好的事兒啊,考古和哲學(xué),冷門是冷門,但山大是個(gè)好學(xué)校啊。”
“嗯……”
“機(jī)會(huì)很難得的。”
“我再想想吧,謝謝老師。”
一個(gè)月回趟家,跨上沉笨的黑色大自行車,吹起十幾公里荒涼的野風(fēng),然后再準(zhǔn)備幾罐炒疙瘩咸菜和足夠斤兩的煎餅,又是十幾里的顛簸。
而她的疼痛,她對(duì)未來的憧憬以及所有的青春時(shí)分獨(dú)有的幻想,或許只有路旁家槐聽到了其破土而出的窸窸窣窣聳動(dòng)聲。干癟的青春忽而到了窮途末路,又似乎仍有一絲轉(zhuǎn)機(jī)。
下一次再次面對(duì)班主任,她直言拒絕。
考古與哲學(xué),對(duì)于那個(gè)年齡的她來說過于遙遠(yuǎn),她還沒有足夠的眼界去思考這兩個(gè)專業(yè)日后會(huì)怎樣在未來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dāng)傻孩子也面臨高考志愿的難題時(shí),她聊起那個(gè)時(shí)候自己對(duì)于考古的印象竟然僅僅停留在是個(gè)挖“尸體”的專業(yè)、不好賺錢,嘴邊出現(xiàn)那種苦澀的表情,但轉(zhuǎn)瞬即逝,似乎只是有關(guān)緬懷過往的苦澀。
一九九五年,高考考場(chǎng)上,十九歲的她第一次接觸英語聽力。
高中三年,她從未見過“聽力”這種東西,然而報(bào)考英語專業(yè)是要考聽力的,雖然熱愛寫文章和看書的她也一直是以中文相關(guān)的專業(yè)作為自己的夢(mèng)想。自己是語文課代表,高一高二時(shí)在四百多名學(xué)生的寫作比賽中拿個(gè)第一輕輕松松。
放棄了保送,放棄了中文,她報(bào)考的是英語專業(yè)。自己連個(gè)像樣的收音機(jī)都沒有見過,又提什么英語聽力?
然而就是這樣,她跌跌撞撞闖入師專。
“我們那時(shí)候有個(gè)說法,未來社會(huì)的三個(gè)目標(biāo)是英語、法律和會(huì)開車。”她一本正經(jīng)向傻孩子解釋道。
“那么事實(shí)上,現(xiàn)在的你是個(gè)初中英語老師,對(duì)法律也略知一二,手握駕駛證而且有輛體面的車。”傻孩子笑道。
“他們都說學(xué)外文很賺錢。”她補(bǔ)充說。
“沒事,你做的很好。你看,你都實(shí)現(xiàn)了啊,這太厲害了不是么。”傻孩子在視頻電話的另一端尷尬地來回踱步,“話說,你大學(xué)花銷怎么解決呢,我知道,不,我是說感覺那個(gè)時(shí)候你們同齡人……”
“當(dāng)家教哇。”她的語氣又輕松起來,“賺了不少零花錢呢。”
“嗯……”傻孩子回想起大一時(shí)舅舅路過自己上學(xué)的城市出差,他執(zhí)意邀請(qǐng)傻孩子前往他暫住的酒店見面,而碰頭后,舅舅塞給她五千塊錢。
自己定是不敢收下。
舅舅他掐滅煙,解釋說自己上高中、大學(xué)時(shí)傻孩子的母親總是寄給他生活費(fèi)還有各種零用錢。這種事情她從不吭聲,在那個(gè)時(shí)候身為獨(dú)生女的傻孩子才猛然記起——
自己的母親還是兩個(gè)人的姐姐。
在那個(gè)年代,她學(xué)會(huì)自己保護(hù)自己,幾乎不再奢求他人能夠給予幫助,但仍毫不吝嗇地關(guān)愛著周圍的人,并且不求回報(bào)。
事實(shí)證明,她的性格很適合當(dāng)老師,雖談不上偉大得桃李滿天下,但足夠?qū)Φ闷鹜卩l(xiāng)下滾打的孩子們,夢(mèng)種下了,可還需自己來傾心澆灌。多年之后的一次大掃除,傻孩子發(fā)現(xiàn)了一封干凈的信,保存得相當(dāng)仔細(xì)。
傻孩子以為應(yīng)該是她青春時(shí)收到的情書之類的趣物,但真正打開來后卻是密密麻麻的英文,是封英文信。
“那是我大學(xué)老師寫給我的。”她倔著性子保護(hù)起其他信件,“她是個(gè)老美,很有意思。”
“你們還有外教?”傻孩子瞪大了眼睛。
“有哇,怎么會(huì)沒有,正兒八經(jīng)的老外呢,三十五歲左右。我們經(jīng)常和她一起玩,陪她過節(jié),陪她逛街,她還去過泰山國際登山節(jié),這是當(dāng)初她寄給我的照片。”
“那之后呢?”
“什么之后?”
“畢業(yè)之后你們就沒有再聯(lián)系了嗎?”
“沒有了,或許她退休回國了吧?也有可能中途去干了別的事情。”
當(dāng)年偶然談起她的外教老師,傻孩子滿是羨慕。但不曾料到大學(xué)之后,自己專業(yè)的口語老師便是個(gè)愛爾蘭姑娘。
在教室坐下的那一刻,傻孩子就仿佛變成了自己的母親。再到后來的大三大四,各種各樣的外國老師授課讓傻孩子才真正感受到了雙語的折磨。她是不是也有類似的體會(huì)呢?她是不是因?yàn)橛蓄愃频捏w會(huì)才會(huì)選擇讓傻孩子報(bào)考這個(gè)專業(yè)呢?經(jīng)歷過,所以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足夠的能力與勇氣去克服,會(huì)受的疼痛自己也知曉一二。
傻孩子曾設(shè)想,她這么努力,是不是不希望過去自己的覆轍讓傻孩子重蹈。
她對(duì)佛學(xué)倍感興趣,雖然傻孩子不像她那般深入研究,但仍懷敬畏之心。迄今為止傻孩子總感覺自己的生命脈絡(luò)與她交織緊密,有些事情冥冥之中又總該那樣,亦或者荒誕到難以置信。
找不到答案時(shí),傻孩子會(huì)將解題的思路全然托付于此。
“你第一次賺錢后買的東西是什么?”傻孩子開始沒話找話地問。
“第一次賺錢買的東西?記不清了,買了錄音機(jī),你舅舅上高中學(xué)英語要用啊,這是個(gè)好東西。還給你姥爺姥娘買了血壓計(jì),買了手表。”
聽到“姥爺”二字后,傻孩子慌慌張張地岔開了話題。
都過了一年,傻孩子還是對(duì)此顧忌萬分,傻孩子開始暗罵自己的矯情與怯懦。
一九九七年,她畢業(yè)了。七月份畢業(yè),八月份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緊湊。
至此,傻孩子感覺她的生命就仿佛啟動(dòng)了埋藏已久的加速鍵。剛工作她便是班主任,朋友圈里她的第一屆學(xué)生們的孩子大多都到了傻孩子的母親所教學(xué)生的年齡。
九九年,在熟人的說媒下結(jié)了婚;二零零零年懷孕;零一年的一月,順利生了傻孩子,就在這庚辰龍年的尾巴。
女孩。
母女倆恰巧差了兩輪。
傻孩子和她就仿佛鏡子的兩面般,相似但又相反,她過去如飽嘗多么多么繁重的艱辛與貧窶,那么傻孩子將會(huì)擁有于此相同甚至更多的幸福與快樂。
有時(shí)候,傻孩子恨自己明白得太晚。
“你知道嗎,我是離預(yù)產(chǎn)期有七天時(shí)才不上課的。”
“欸?”
二零零四年,在煤礦上班的傻孩子的父親下崗了。
她雖然是個(gè)鄉(xiāng)村初中教師,收入磕磣的,但還算是穩(wěn)定。傻孩子的父親便一邊帶孩子,一邊打些臨時(shí)工,有時(shí)候會(huì)去南坡的紙業(yè)那邊干活。
在傻孩子出生之前,她和另一半住在婆婆公公家,兩人都是近近遠(yuǎn)遠(yuǎn)地趕班。但思前想后那七十多平米的頂樓將來要容納五個(gè)人,終歸是令人身心俱疲。
于是當(dāng)孩子八個(gè)月大時(shí),她拍板了,提出來在傻孩子父親工作的莊買個(gè)房。
就仿佛有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神力,她每逢家庭大事時(shí)做出的決定永遠(yuǎn)是那么正確。
可那么一想,那年她放棄保送名額的決定又是否正確?
決定買房的那年,她也進(jìn)行了工作調(diào)動(dòng),從另一莊的學(xué)校調(diào)到了傻孩子父親工作的那個(gè)莊的學(xué)校。說來巧得不得了,她打算換工作位置的時(shí)候,目的地莊學(xué)校的一個(gè)英語老師恰好想調(diào)到母親想離開的地方。
似乎那位老師對(duì)這個(gè)莊的生活條件并不是很滿意。
但無論怎樣,你情我愿的事情天底下太難找,既然碰到了,那么二人都順順利利地實(shí)現(xiàn)了愿望。
此后,她便在這個(gè)莊的學(xué)校工作了二十多年,與孩子一起,也見證這里的興起、發(fā)展與衰敗。這里的人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他們很多孩子都是她的學(xué)生。鎮(zhèn)子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隨著日子越來越長,人們大多是成于此莊也敗于此莊。
往返爺爺奶奶家路上一個(gè)半多小時(shí)的公交車路上,有座黑不溜秋的小山丘,她和傻孩子都喜歡叫它“渣子山”。
然而廠礦不是長久之地,與亦如積落的煤灰一同隨風(fēng)消逝,這個(gè)以煤礦發(fā)跡而又受困于煤礦、沒落因煤礦的小鎮(zhèn)村莊也會(huì)消失。
最后沒有人再會(huì)講它的故事,回憶它的過去。
二零零八年左右,傻孩子的父親去內(nèi)蒙古的煤礦打工了,小小協(xié)莊的煤礦生產(chǎn)力終究再也追不上當(dāng)今發(fā)展的飛速,轉(zhuǎn)型總是乏力到困倦。他也終于是有了個(gè)踏實(shí)的飯碗,這還是托了她的關(guān)系的福。
傻孩子一直認(rèn)為父親下崗在家的那段日子是自己最快樂的時(shí)光,年幼的傻孩子對(duì)于下崗并沒有什么概念,只知道他每隔幾天下午便會(huì)帶自己去南邊的小廣場(chǎng)瘋玩,看著傻孩子在石頭堆里仿佛一只小老鼠傻乎乎地般上躥下跳,?站在大秋千的背后送傻孩子蕩蕩擺擺去觸摸星月,與傻孩子比拼誰玩健身娛樂器材玩得花樣多。
傻孩子不知道那個(gè)時(shí)候的她壓力究竟有多大,只知道自己和她都喜歡一直穿著姑姑家的舊衣服,只知道自己和她都喜歡不吃零食不買化妝品,只知道自己和她依舊滿懷笑聲。
晚上傻孩子和父親會(huì)去北面的大廣場(chǎng)找其他伙伴們耍到十點(diǎn)十一點(diǎn),在充足了氣的蹦蹦床樂園里翻來滾去,付了幾塊錢后,他被拴在樂園的大拱門外拎著水杯聽那鼓風(fēng)機(jī)發(fā)出巨大的噪音。
這個(gè)時(shí)候,她便會(huì)在家里守著一用就是十幾年的長虹彩電織毛衣。小時(shí)候傻孩子很少有新衣服穿——當(dāng)然新年時(shí)除外,衣柜里有不少衣物是傻孩子表姐的舊衣服或者爺爺奶奶從要好的鄰居那里“撿”的。
她十分擅長縫紉,對(duì)于她來說也許所有令同事朋友們所贊嘆不已的技能都是受生活逼迫后學(xué)會(huì)的。
那些舊衣服,她總能針針線線魔法般得讓它們合身起來。依稀記得有幾個(gè)夜晚,鍋里咕嘟咕嘟滾著漿糊,她用那些平日里攢的破布頭開始糊鞋墊布,按照舊鞋墊的大小用鉛筆畫出輪廓,黑色的大鐵剪刀咔嚓咔嚓,再用碎布收邊,舞著五彩的線秀出好看的圖案。
有一件成品的斜領(lǐng)毛衣,因?yàn)樾r(shí)候留馬尾的傻孩子討厭套頭衣物,但勉強(qiáng)接受這個(gè)帥帥的款式毛衣。她用舊毛線團(tuán)照葫蘆畫葫蘆,織了件一模一樣不同顏色的出來。
也許這些事情并不稀奇,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總讓傻孩子驚嘆不已,而且這種場(chǎng)景就對(duì)于當(dāng)下來說也早已不再常見。
這些似乎平淡無奇、看慣不驚的細(xì)節(jié),都是過去那個(gè)孩子獨(dú)一無二的回憶。如果未來傻孩子的孩子期待傻孩子親手為她織出一件衣物,她很有可能會(huì)期待落空吧。
織手套、圍巾、毛衣毛褲是如此簡(jiǎn)單,甚至連傻孩子曾經(jīng)冬日穿棉衣棉褲都是她親手測(cè)量裁布塞棉花制成的。再到后來,當(dāng)衣服這里工業(yè)品廉價(jià)到家庭手工已沒有必要節(jié)約時(shí),她也終于告別了那個(gè)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七十年代三大之一縫紉機(jī)。
不過即便如此,現(xiàn)在她仍然自己縫被套和做床單。
等傻孩子上大學(xué)后,她總是為傻孩子購置新衣服,然而傻孩子也像她般保留了過去那對(duì)新衣物欲望不高的習(xí)慣,但即便傻孩子怎樣拒絕她買衣服的提議,卻還是常常收到快遞。
“媽,你的腳指頭怎么都是畸形的?”傻孩子無意間問道。
“小時(shí)候沒有合腳的鞋,都是別人穿剩下的。”
傻孩子頓時(shí)緘默不言。
當(dāng)傻孩子還是上學(xué)時(shí),冬春季節(jié)時(shí)她對(duì)于傻孩子是否會(huì)在出門前涂抹護(hù)手霜與護(hù)臉?biāo)⒐⒂趹眩岛⒆硬恢獮楹螛O其厭惡這種油乎乎、滑膩膩的乳膏,所以總會(huì)時(shí)不時(shí)趁她不注意時(shí)偷偷糊到家里的大白墻上,并且竊喜自己的小聰明。
直到十五多年后,當(dāng)初那個(gè)自作聰明的傻孩子在南國冬日臺(tái)風(fēng)臨近的濕冷寒夜里突然打了個(gè)寒顫,傻孩子突然想起來她因?yàn)殚L時(shí)間粉筆板書而皸裂至滲血的手指。
原來所有瑣碎且無微不至的關(guān)切,都來源于不易發(fā)覺但隱隱作痛的傷口,野孩子之前疼過,所以才知道如何處理傷口和保護(hù)。
她之前受過凍,所以不想讓傻孩子挨到冷。
這是她關(guān)于過去難以釋懷的體現(xiàn)么?
有些事情,雖然傻孩子與她都不明說,但它們儼然梗在大家的心頭,隱隱作痛,就宛如扎入指肚的小刺頭。
傻孩子對(duì)于自己降臨于世之前的風(fēng)和雨全全不解與難以想象,等而后慢慢長大眼睛可以看清東西,試圖用刀匕撬開木板去窺那些被時(shí)間攔住的景象,因?yàn)閺耐饷鎭淼娜酥v得五花八門,屋里聽得天花亂墜,有些心頭亂顫,手指頭發(fā)熱,挽著嫩草根在順滑的白紙亮面寫下比天花亂墜更甚者的跳舞小人,最后嫩草根都折腰在她們面前。
而傻孩子還在努力伸長著脖子試圖探點(diǎn)什么,但始終被圈在同一個(gè)框框間,但敬畏之心總懸在頭上,于是傻孩子望向她,她也望向傻孩子,眼神淌出一條蜿蜒曲折的溫潤溪流。
某個(gè)夏日,或許小學(xué)的傻孩子還在放暑假,傍晚她沒有做飯,也有可能兩人已早早吃下,傻孩子實(shí)在記不真切了。
但現(xiàn)在仔細(xì)回想,她大概就是因?yàn)樯岛⒆硬粫?huì)牢記太多小時(shí)候的記憶,而選擇在那天進(jìn)行此事吧。
兩人出門了,她說帶傻孩子去南坡干點(diǎn)事情,晚上出去玩時(shí)常有的事情,曾經(jīng)傻孩子的父親下崗在家時(shí)也喜歡這么做。
她沒有直接說出此行的目的,然后牽著傻孩子的手在村南邊的小雜貨鋪買了個(gè)廉價(jià)的長面包,平時(shí)吃不上零食又饞嘴的傻孩子自然是歡喜得不行,同時(shí)她還買了打火機(jī)、一點(diǎn)黃顏色的紙與黃顏色的焚香。
將近初中后傻孩子才知道,那叫“錢糧”,是祭拜時(shí)用的。
荒地上的野草與野花守住母女二人的小秘密,火與紙靜靜地燃燒,孩子與孩子的孩子靜靜地長大。蒙蒙冷風(fēng)圍繞著灰色的鄉(xiāng)村矮房,上面頂著灰色的天,下面踩著灰色的地,煤礦粉塵打著轉(zhuǎn)。
她選了個(gè)偏僻的從間的空地,異常簡(jiǎn)陋,但下一刻她跪上去了,說著什么,而后傻孩子也跪上去磕了幾個(gè)頭。
那個(gè)時(shí)候傻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回去的路上她沒有補(bǔ)充解釋,日后再也沒有提過,也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傻孩子也一樣,只是默默地記著,不會(huì)主動(dòng)提及,但每每回憶,她那個(gè)時(shí)候沒有哭泣,傻孩子多年不曾見到她的眼淚。
這是傻孩子第一次為那位母親的母親而進(jìn)行祭奠,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長大后的傻孩子依舊裝作什么也不懂,就像每次談及敏感話題時(shí)自己每每避免目光的碰撞而打攪到她內(nèi)心深處最容易受痛的地帶。
究竟是怎樣的女性才能誕下野孩子這聰慧、負(fù)責(zé)任且有勤勞的母親,該問至此已成無解之題,因?yàn)榛蛟S那位女性的身影也在傻孩子的母親的記憶里愈行愈遠(yuǎn)。
想到這里,傻孩子就開始不爭(zhēng)氣地替她默默抽泣,但不解其因。
極遠(yuǎn)之處浮動(dòng)著一團(tuán)團(tuán)光芒低沉的亮點(diǎn),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傻孩子耳旁突然再次響起那句“以后我就沒有爸爸媽媽”,那句話說畢后,她開始為了傻孩子而存在,為了自己而存在。
“這一次,我?guī)慊丶摇!?/p>
鈷藍(lán)色的夜空中稀疏的星辰似乎在吟唱古老的歌謠,嘆息著、照亮她尋回故里之路的過程,她以過客的身份重新造訪孩童時(shí)熟悉的土地。
曾經(jīng)用青春耕犁的土地還在老院門外,院內(nèi)撞入眼簾的是棵矮小的山楂樹,那年野孩子帶孩子返鄉(xiāng)探親時(shí)老人親手所植,如今它抿塵吮露,枯枝爛葉的軀體潰瘍處爆裂出點(diǎn)點(diǎn)紅。
忽然,天上的星星對(duì)她說道,“別追了,別追了。”
野孩子抬頭望向夜空。
天上的星星對(duì)她說道,“別愛了,別愛了,什么時(shí)候你開始的依依不舍。”
野孩子低頭望向老宅。
“別追啊,別追啊,你為什么還在依依不舍。”
野孩子緘默不言。
“天上的星星再也不會(huì)回來,你在依依不舍什么?你在苦苦等待什么?”
從她淺淺的腳印到每一條鉛灰色的屋脊、每一棵冷峻的家槐、每一道嵌入土地的車痕,她都熟悉,然后遽然全全都陌生起來,與家鄉(xiāng)冥冥聯(lián)系著的線繃著繃著,斷掉了。
隨著那根線斷掉的,還有那些聲音,從此她再也沒有聽到過天上的星星講的話,然而她依舊在依依不舍,依舊在苦苦等待,依舊在為了那些不再回來的而存在。
來年,傻孩子問她想不想看海潮澎湃,問她想不想看鳳凰花開,問她想不想看騎樓莓苔,問她后悔不后悔當(dāng)初的選擇與等待,她堅(jiān)定而果斷地回答道,想看。
初秋,卻天寒地凍。南國的四季如春向北飛回是如此困難。
她的父親自殺后,她把骨灰抱了回來,與自己已逝多年的生母葬在同一處。
持續(xù)了將近四十六年之久,那是令人驚悸錯(cuò)愕且心如刀絞的四十六年,同時(shí)也是重新審視自我與找訓(xùn)自身價(jià)值的四十六年。叵測(cè)的命途,越是逃離,越是會(huì)接近,而那日漸模糊的背影襯著逐漸衰弱的燭火被無限地拉長,最終延展成一座橋,一座窄窄的、單向的、歲月斑駁的獨(dú)木橋。
清亮的路燈透過窗戶,明明是夏末之夜,卻冷得令心房緊縮。那晚,她說自己又一次少了個(gè)家。
痛苦到要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那究竟是怎樣的痛苦?
她百思不得其解,但答案又觸手可及。
傻孩子相信,她對(duì)于自己父親——傻孩子姥爺?shù)碾x世,一定是愧疚之情遠(yuǎn)超于思念之情。傻孩子甚至相信,還有很多同她相似的人也在經(jīng)歷著相同的事情,被相同的感情所折磨到夜不能寐。
父母用自己的半生,成就了孩子的一輩子。有人說,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處;父母去,人生只余歸途。確實(shí)如此,陰陽兩相隔讓親情升華至極點(diǎn),但同時(shí)也使其成為絕唱。
于是,聰慧的她開始更加愛身邊的人。
她與傻孩子所見過的其他母親相比,真的太愛自己的孩子了。傻孩子見過有的母親將自己的教育失敗推卸給私塾教育,傻孩子見過有的母親將孩子送到不正規(guī)的夏令營后自己游山玩水,傻孩子也見過有的母親過分溺愛孩子繼而溺死了他們。
她愛傻孩子,而且愛得果斷且正確。
現(xiàn)在再想,可能是她想把自己年幼時(shí)起就缺失的那份母愛連同自己的那一份母愛,一同給予自己的下一代吧。
“媽,你寫點(diǎn)東西嘛。”
“你便是我最好的作品。”
“媽,你年輕的時(shí)候有什么喜歡的東西嘛?”
“漂亮衣服,漂亮的筆記本,課外書。”
家里的柜子里塞滿了各種樣式的筆記本,皮的、花紙的、封面帶花的,都是她囤的,都是她在辦公時(shí)省著省著攢下來的。
她囤給傻孩子用,但估計(jì)她也沒想到傻孩子同樣喜歡囤筆記本。
囤積的習(xí)慣傻孩子和她誰也改不掉,當(dāng)時(shí)傻孩子家甚至連電動(dòng)車都不買,兩條腿走遍了鎮(zhèn)子,去遠(yuǎn)點(diǎn)的地方就擠公交車,然而傻孩子家離公交站點(diǎn)還要走半小時(shí),這段路程對(duì)于年幼的傻孩子來說是有些煎熬,再遠(yuǎn),都是走著,幾塊的三輪車錢能省就省。直到現(xiàn)在,她依舊堅(jiān)持手洗衣服。而傻孩子也是,宿舍她們買了洗衣機(jī),傻孩子則是保持著手洗的習(xí)慣,無論床單還是褲子T恤。
舍友善意地表示傻孩子如有需要,隨時(shí)可以借用。
傻孩子則是滿懷感謝之情地婉拒了舍友的善意建議,那一刻傻孩子才下意識(shí)發(fā)覺,并猛然驚呼,即便早已不再朝夕相處,但父母所潛移默化影響我們的種子,隨著我們的長大在悄悄生根發(fā)芽,然后伴著我們的一言一行破土而出。
她從來不掩飾自己對(duì)于同事們更加優(yōu)越生活的羨慕,但她又不酸溜溜耍嘴皮功夫,她承認(rèn)自己的另一半賺錢比其他熟人的老公賺錢少,但她還會(huì)開源節(jié)流。
傻孩子初高中時(shí),她全款在市中心的高新區(qū)買了套房,又自己主持著完成全部裝修。那個(gè)時(shí)候傻孩子腿傷、中考,老人心理疾病剛剛有跡象,她還考下了駕照,同年又解決了高中傻孩子跑校住宿的出租屋。
緊接著,她又在市區(qū)的另一邊規(guī)劃休閑度假區(qū)的附近買下個(gè)面積更大的毛坯房。
傻孩子大一時(shí),她又在莊附近的山腳下小區(qū)購置了套依山傍水的房子,自己設(shè)計(jì)、自己找人裝修,很快便帶著自己的貍花貓“有財(cái)(才)”住了進(jìn)去。
第二年,她又從同事那里領(lǐng)養(yǎng)了只小黑貓,取名“有福”。
傻孩子從來沒有想象過家庭情況的改變竟然是如此巨大,她亦從羨慕同事的角色變?yōu)榱藗涫芩齻兯w慕的角色,然而對(duì)此她只是一笑而過。
喜歡茶的她為自己設(shè)計(jì)了個(gè)房間作為茶室,桌邊便是今年剛冒了星星點(diǎn)點(diǎn)白花的文竹,對(duì)面是擺放了弟弟弟媳和小侄女照片的書架,書架旁的窗臺(tái)安然趴著只十斤有余的肥貓被屋外鳥語花香吸引得目不轉(zhuǎn)睛。
最后傻孩子發(fā)現(xiàn),能治愈自己的始終還是自己,傻孩子的母親需要與自己和解,而傻孩子則需要同她進(jìn)行一場(chǎng)陪跑。
父母是很多人的心結(jié),她亦如此,傻孩子亦如是。
愈是說,愈是寫,愈是刻意回避或無心提及,都是百般思念、萬番情緒。
她一如既往般得披堅(jiān)執(zhí)銳,打理著紛至沓來的蕪雜情緒,獨(dú)自喝著自己煮的粥,獨(dú)自清掃著自己房子的灰塵與貓毛,獨(dú)自按照自己的作息早出晚歸,獨(dú)自做自己的夢(mèng)。
無力償還的善良與奢侈的愿望盛開出果實(shí),那是異常飽滿且圓潤的果實(shí),汁水充沛,沁甜如蜜,然而最后好奇的野娃子剝開果肉里裹挾隱匿的核,野娃子驚訝于其質(zhì)感的堅(jiān)硬與細(xì)膩,頓感心中酸楚翻涌。
野娃子翻來覆去地?fù)崦麑?shí)的核兒,眼中打著轉(zhuǎn)的淚澆灌出沃野千里,而那個(gè)富有智慧、情調(diào)與機(jī)會(huì)的種子則深入泥土,在星空下燃燒著,在朗日下發(fā)出震耳欲聾的爆裂聲。
她一定會(huì)長命百歲的,連同她身邊所有令人倍感遺憾的事與人,精彩萬分地活下去,享受過去吃苦受累后努力誕生出的甘美結(jié)果。
“你爸十二月的時(shí)候做了個(gè)手術(shù)。”
“什么手術(shù)?”
“有個(gè)瘤子。”
“哪里的?”
“肚子里,好像是腸道那邊?體檢的時(shí)候查出來的,已經(jīng)沒事了,恢復(fù)得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我松了口氣。因?yàn)槁吠酒v,我很快就沉沉睡去,路途依舊,路途旁的風(fēng)景依舊,耳邊有家鄉(xiāng)的冷風(fēng)呼嘯而過的響動(dòng),也有她平靜、細(xì)微且均勻的呼吸聲,我非常喜愛這種聲音,就仿佛追求生命溫暖與幸福時(shí)奔跑的腳步聲。
說到底,是私情,是小愛,全全不是什么滔滔不絕的洪流洋海,或許對(duì)于她來說才可成為綿長、糾纏且荒涼過又富饒著的人生,而我不過是僥幸窺見煙火一縷的多情的頑童。
也正是如此,我愿意為這煙火的燃續(xù)奔赴而入那名為生活的紛亂柴堆之中。
[責(zé)任編輯:linlin]
相關(guān)文章
-

天天觀熱點(diǎn):究竟是徒有其表,還是內(nèi)有乾坤——聊一聊《瞬息全宇
-

環(huán)球播報(bào):【童話/寓言】解藥
-

天天觀點(diǎn):【丑小鴨】
-

全球微動(dòng)態(tài)丨【故事新編】圣誕老人的禮物
-

每日觀察!森林幻想曲
-

焦點(diǎn)消息!在失眠的夜晚,我又打開了《糖豆人》
-

視焦點(diǎn)訊!“我們的幸福生活” 短視頻征集展示活動(dòng)正式啟動(dòng)
-

今亮點(diǎn)!【睡前故事】海的女兒之人魚的謊言
-

當(dāng)前熱點(diǎn)-【童話新編】小美人魚
-

【全球熱聞】翻譯翻譯,什么叫情書?情書就是翻一翻……
-

【環(huán)球報(bào)資訊】小紅帽的故事
-

天天實(shí)時(shí):不是豪門媳婦嗎,怎么又出來掙錢了?
- 1 國家藥品集中采購倒逼藥企殺價(jià)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jī)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dòng)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用車廂 到底有無必要?
- 10 教練長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實(shí)名舉報(bào)
- 1 國家藥品集中采購倒逼藥企殺價(jià)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jī)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dòng)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用車廂 到底有無必要?
- 10 教練長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實(shí)名舉報(bào)
- 房地產(chǎn)業(yè)或迎融資"緊箍咒" 多家房企積極表態(tài)
-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活動(dòng)
- 中央軍委訓(xùn)練管理部四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著裝辦法》退役軍人可以在公開場(chǎng)合穿軍裝了
-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了
- 85歲老黨員不顧危險(xiǎn)跳水施救82歲落水老太
-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六大關(guān)鍵詞讓你了解蘋果新品發(fā)布會(huì)
- 蘋果今天發(fā)布了 Safari 技術(shù)預(yù)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fā)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cái)年第三季度財(cái)報(bào)-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fā)布會(huì)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diǎn)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cái)年第三季度財(cái)報(bào)-全球今亮點(diǎn)
- DLSS 功能測(cè)試已支持英偉達(dá)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shí)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zhàn),雖然是個(gè)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jī)會(huì)-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gè)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zhì)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dòng)態(tài)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fā)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diǎn)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jiǎn)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dòng)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diǎn)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tái):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diǎn)日?qǐng)?bào)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huán)球觀天下
- 高等數(shù)學(xué)(上)習(xí)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diǎn)上線 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zhuǎn)函數(shù)-當(dāng)前要聞
- 鄉(xiāng)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nóng)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jié)對(duì)共建助力新時(shí)代文明實(shí)踐
- 植宗山茶油發(fā)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yǎng)豐富哦~
- 金秋時(shí)節(jié)正是吃板栗的好時(shí)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dāng)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diǎn)
- 林志穎妻子回應(yīng)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shí)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huán)球報(bào)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nèi)容大變買個(gè)ip網(wǎng)劇套原創(chuàng)劇利用書粉基礎(chǔ)宣傳-全球聚看點(diǎn)
- 蘇感加倍來襲,養(yǎng)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dú)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yù)售日10月24日進(jìn)行淘寶直播首秀-環(huán)球新資訊
- 養(yǎng)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fā)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yǎng)頭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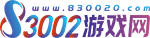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píng)論員文章
評(píng)論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