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有記憶開始,來家便彌漫著一股劣質酒精的味道。這種味道在雜亂的小院子久久無法揮發,只能打著旋兒,從這頭飄向那頭,再從那頭飄回來。年幼的來生提著一個與身體極不相符的木制桶,踉蹌著往廚房奔去。
說是廚房,不過是用四根破舊的手腕粗細的棍子搭建的簡易的小帳篷,上面鋪了一層薄薄的稻草,下雨時又濕又重。有時候雨下得大了些,稻草便一股腦兒落下來,在雨水的浸泡下逐漸流出發黃的液體,形成一股黃黃的細流與渾濁的水匯成一道大些的溪流流向門外。門外是一條泥濘的小道,周圍并沒有人家,正前方是個大坑,日子久了存了好些水,有時也能摸出來幾只泥鰍。
來生曾問過爹,那坑怎么來的?來生爹舉著酒罐子,朝黑洞洞的門外看了許久,終于說,給老子滾去睡覺。來生不敢說話了,只悶聲回了房間。老舊的房子只有一個房間,房門正前方放著一張八仙桌。桌子一米多高,黑漆,描了金色的邊,若是放在以前定是風光無限,可是,在歲月的侵蝕下,黑色變淡了,金色也幾乎看不出來了。不過,它一直在房間正中間,這是不管怎么變都沒有辦法撼動的地位。八仙桌左右兩邊分別隔了一張簾子,各放了兩張床。來生住左邊,右邊按說應該是來生爹和娘一起住的,不過來生并沒有見過娘,記憶中只有爹的樣子。
來生曾問,爹,娘呢?來生爹將酒罐子狠狠摔在地上,隔了許久,終于說,給老子滾去睡覺。來生說,爹,白天不想困覺。來生爹一時語塞,默默地撿起酒罐子,去了酒館。
爹不在家的時候,來生只做一個人的飯。這么多年,不管是做飯還是炒菜,來生都熟練了。唯一不能接受的便是這比他還重的木桶。水是從離家幾百米的井里打上來的,笨重的水桶去時是空的,還算可以,來時卻有了重量。來生只能走幾步歇一會兒,走幾步歇一會兒。半個多小時才終于到家。每次打水,總能遇上幾個奇奇怪怪的人圍在身邊。他們穿一身官府的衣服,戴著紅頂子,手拿一根棍子。那棍子又亮又滑,經過無數人鮮血的浸染仿佛有了生命,整日里耀武揚威地望著來生。來生并不怕他們,只低著頭,哼哧哼哧地搬弄水桶。那些官爺也不理他,只遠遠望著,偶爾吹個口哨,卻不說話。
來生將水桶放在廚房,看看黑黝黝的鍋,嘆了口氣,吹了火折子準備生火做飯。這是很平常的一天,爹照樣不在家,火折子照樣怎么都吹不著,連來生的大花臉都跟昨天一個樣。來生吹了很久,始終不見火星,終于生氣了。他抬腳準備將水桶踢倒,想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提了這么點水,實在有些舍不得;又抬腳準備朝廚房的柱子踹兩腳,又想想這柱子倒了,以后下雨連飯都吃不上了......那只黑乎乎的腳抬起又放下,來生實在沒辦法,只能使勁蹦了兩下,算是解氣了。
灰塵被夏天的風吹起,打了幾個旋兒終于消失不見了。外面幾個官爺也終于結束了一天的偵查,正準備打道回府,卻看到不遠處來了一匹馬。這馬通體雪白,黑色的馬鞍更是顯眼。官爺愣了一下,他們自然知道這白馬是縣太爺的愛物,此時來自然有事。
幾個人站定了,不一會兒功夫,馬長叫一聲,高高抬起馬蹄,又重重放下。“幾位爺,縣太爺有令,緝拿來家那小子回縣衙。”尖嘴猴腮的師爺氣喘吁吁的說。他一介文人,從沒在馬上狂奔過,如今若不是衙門沒人了,怎么也輪不到他一個師爺出來奔波。一想到衙門的事,他不由得皺了皺眉,說:“我還有事,先走了。”
幾位官爺拱手送走了師爺,罵罵咧咧地開始了。一個說:“老子一天到晚在這里喝風,他倒好,一撅屁股走了。”一個說:“這王八蛋指定拍縣太爺屁股去了。”另一個說:“算了算了,拿人吧。”
一行人幾乎沒費吹灰之力就踹開了來生家的門。說是門,不過是兩塊板子拼成了門的形狀,怎么經得起臨門一腳呢?門倒下的時候,揚起了一陣灰塵,風將灰塵刮走時,幾個人只看到來生正傻乎乎地又蹦又跳。他們哪里知道來生正因為吹不著火折子生氣呢!
“走!跟我們走一趟吧!”一行人惡狠狠地說。
來生愣了一下,轉身想跑,卻又擔心好不容易提來地水被他們糟蹋了。正猶豫時,人便被套走了。那是來生第一次進牢房,官爺還算不錯,只罵罵咧咧,推推搡搡,并沒有真動手。來生被推進了一個單人牢房,厚厚的稻草散發出刺鼻的味道,有些地方還滲出水來,不知道是房頂漏的水還是其他別的東西。來生捂住鼻子,大聲叫:“抓我干什么!”他喉嚨已經啞了,一路上吵吵嚷嚷讓幾位官爺煩透了,卻又不能說什么。這是上面交代的事情,網下了很久如今好不容易收網了,卻忽略了這小子竟是一個既會說話,又會胡鬧的主。
來生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總繞不過那桶水。有時說得多了,總記不住自己怎么就到了縣衙的牢房。其實,說到底,來生那時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沒有被嚇暈已經很不錯了,至于記憶中出現的一些出入,總能被人原諒。
二
來生爹總是天黑透了才回家。回家的時候總是一手拿著酒罐子,一手隨著身體的踉蹌上下左右晃動,偶爾還會朝碩大的、光禿禿的前腦勺拍上那么一下。每次經過門口那大坑,來生爹也總會習慣性站那么一會兒。大坑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它存在之前,門口有三五戶農戶,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雖然清苦,卻也算平靜。那,是什么時候變了呢?來生爹也不清楚。只聽說,某一天縣令從外面帶回了一個寶貝。年輕的來生爹跟朋友自然好奇,一個個放下鋤頭非要去看個究竟。來生爹后來總想,若是那日他們不去看熱鬧,事情會不會好一些。
上天怎么都不會給他們再次選擇的機會。那一天,來生爹跟幾個農戶放下的鋤頭,跑到了縣衙門口看熱鬧。那是個通體黝黑的家伙,肚子大,頭長,幾個官爺拿著棍子圍成了一個圈。其實,就算是不圍著,也沒有人敢靠近,畢竟人對新生事物有著天生的好奇心與敬畏感。來生爹就那么盯著那鐵疙瘩,看了一會兒,頓覺得沒意思,便招呼著人想走。誰曾想,縣太爺出來了。這個滿臉胡子,無比尊貴的人大喝一聲,隨后拱手做了個揖,清了清嗓子,說:“諸位相鄰。近日我大清于南京與英簽訂了《南京條約》,此條約需諸位支持。因此,今年稅收加兩成。”此話一出,一片嘩然。
來生爹頓覺得一口氣從胸腔冒了出來:“去你媽的,讓不讓活!”話一出口,人群便靜了。直到十年后,來生爹依舊能感受到這令人窒息的安靜。他捂住嘴,盯著腳底下看了許久,仿佛這話是從地底下冒出來一般。縣太爺也愣了,他也知道此話沒有道理,卻不得不說。縣衙內知府的文書就躺在桌上,不管是加一成還是兩成又或者是三成,怎么是他這個小小的芝麻官說得算呢?他穩住心,大喝一聲:“方才是誰!”
人群又靜了,所有人都盯著腳底下,似乎這樣便隱去了身體。只是,這堂堂七尺男兒的身體可以隱去,那顆心又如何隱去呢?后來,所有在場的還活著的人都想,若不是官府欺負人,若不是稅收成年累月地增長,若不是......總之,這次加稅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
“我!”
“我!”
“我!”
無數個聲音在死一般的沉寂后爆發了。他們不懂什么條約,也不懂什么官場之事,只知道日子過不下去了。來生爹怎么也想不到,一時興起去看熱鬧竟變成了這個樣子。
坑又是怎么回事呢?來生爹并不清楚。只記得那日回去后,誰也沒有睡。靜謐的夜仿佛與從前無數個夜晚都沒有區別,卻被一聲巨響打破了。巨響之后,村子的人誰也沒動,連點燈的都沒有。夜又恢復了安靜,卻又能從安靜中聽到一縷哭聲。那聲音凄慘、絕望。
“孩他爹,看看去。”來生娘那時剛生產完還不到一個月,最聽不得這樣的聲音,起身催促到。
來生爹心知是白日里嘴快惹下的禍,此時怎么也不敢出去了。他蒙著頭,嗡聲嗡氣地說:“睡,管那些閑事做甚。”
來生娘將耳朵貼在窗戶上,仔細辨認那哭聲,終于說:“怎么像張家嫂子的聲音啊,我得看看去。人家給孩子送了倆肚兜呢!”
說完,來生娘便窸窸窣窣地起床了。黑暗中,她連頭巾都沒戴。夏天的風吹起來也鉆腦子,來生娘從沒想過,這悶熱的夏風竟然這么冷。
來生娘頂著風,終于出門了。剛走到前院張家嫂子家門口,尚未說話,又一聲巨響。一切安靜了。再沒了哭聲,也沒了來生娘。
來生爹聽到第二次響聲出來時,天已經亮了。門板震落了,門口碩大的坑就那么敞在跟前,零星的,殷紅的血雖能看出來,卻已經不甚明顯了。只有聞味而來的蒼蠅,一群又一群。它們在陽光下呼朋喚友;它們在陽光下旋轉舞蹈......無非是為了慶祝這“百年難遇”的大餐。
來生爹跪了許久,淚也流了許久。年邁的村長站在坑前大呼了幾句“造孽啊”便吐血而亡。沒有人指責來生爹,也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沉浸在悲傷中。后來的來生爹變成了這副醉酒的模樣。有人說他們是伉儷情深,有人說他沒出息......總之,來生爹瘋了。
兩成稅加上了,坑也留下了。那一年,整個縣的村子留下了很多大坑。誰也沒填平過,任由這坑逐漸變成水坑......來生爹站在水坑前很久,轉身回了家。此時,他依舊不知道來生已經被抓走了。直到第二天,他依舊不知道來生被抓走了。只覺得少了點什么,后來才反應過來,若是平時,來生早就開始生火做飯了。醉酒后的來生爹對飯并沒有太大的欲望,只當這小子貪玩出去了,竟一點兒都不著急。直到村長來了。新村長已經任職十年了。十年來,他從壯年逐漸變成了老人的模樣。想想不過50歲的人,卻老得不像樣了。年年稅收,年年催,一次多上一成,再好的身體也被熬沒了。
“來生他爹,生子被紅頂子抓走了。”村長摸了摸雪白的胡子,嘆了口氣說,“有人告發了,說十年前你煽動造反。”
十年前。十年前。來生爹愣了。此事過去十年了,竟然還沒過去。
“誰?”
“新知縣。”
新知縣,新知縣。來生想到那個十年前跟自己一起看熱鬧的俊后生,家里出事后便走了。后來聽說他混得還不錯,先是當了兵,后來便打仗立功,沒想到竟做了知縣。是啊,當年一句話,死了幾十條人命。雖然當年的知縣解釋說是幾個不要命的人奪了那鐵家伙試試活,可誰也不信。
如今,來生爹信了。他信因果,信報應,信那個年輕的俊后生是為了給自己的家人討個公道。
來生爹沒有去大牢,徑直去了縣衙。他舉起兩根重重的棍子,朝縣衙的鳴冤鼓上打。一聲,震天動地;兩聲,震耳欲聾;三聲,天翻地覆......
來生爹終于看到了那個戴烏紗帽的男人,滿臉殺氣,舉手投足之間帶著對眼前這個瘦弱、邋遢的男人的鄙夷。
“為何擊鼓?”
“還我兒子。”
“哦?牢房那么多人,都是你兒子?”
“我叫來豐。”
“哈哈哈,來豐!”知縣大人捂著肚子笑了很久。十年前,他不過十多歲,跟著眼前這個男人去縣衙看熱鬧。本來一句話的事,沒想到他竟不承認。誰曾想,夜里他睡得正熟,只聽一聲響,家不見了,爹娘不見了。整個屋子只剩下了他睡覺的那一面沒有倒下。他想,老天爺既然留下他一條命,自然是為了找當年的肇事者討個公道。
“放了我兒子,我還你一條命。”來豐說。
“好。”
三
來生出來了。沒挨餓,沒挨打,只睡了一夜草墊子。
來生出來了。之前沒娘,現在沒爹。滿臉肥肉的知縣,笑盈盈地說:“孩子,抓錯人了。”
來生沒有說話,只瞪了他一眼。
知縣望著孩子遠去的背影,像極了當年的自己。只是,如今他成了知縣......想到這兒,知縣后背不由得生出了一身冷汗。遠去的來生只覺得背上有一道刺,越來越深,越來越大。他抬頭看看灰蒙蒙的天,想:“要下雨了,不知道今年這雨會不會填滿那個坑。”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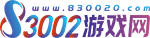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