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后相識,離別又重聚。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矍鑠,有人老去。
年是這一切的輪回,我們想知道一年里別人經歷的那些事,唯有聽說。
1 聽老林說
我聽見老林長呼出一口濁氣,便不自覺地抬起頭,看著這位老教授不見外地在我面前的椅子上伸一個愜意的懶腰,和幾個小時前不一樣的是,桌上那一疊試卷已經從他的左手邊移到了桌面一角,見他把手里的紅筆耍得飛花,我大概是能猜到,他這一學期的教學任務應該是畫上完美的句號了。
老林全名林燦,今年五十有六,年輕的時候是足球省隊的得力主將,退下來之后,便來到我的大學里教體育,帶過校隊的足球,領過七八個教學班的田徑,成績斐然,德高望重,待人也頗為和善,笑必露齒,一口堅挺的白牙能反光,授課好評率常年穩居全校前茅,校園里多數的體育講師見他都得喊聲師傅。
剛入學的時候,班助和我說,體育組里頭有個神人,不管他教什么,你就死心塌地認認真真和他學,上課別劃水,學一年半載,體測的時候別人使出吃奶的勁頭朝著及格線靠,你輕輕那么一跳,最次也在及格線以上。
雖然到最后也沒問清楚那個神人是不是我面前的老林,但和老林學了兩年的太極拳,確實學到不少讓我這個體育白癡很受用的技巧,跑兩千氣也能喘上來了,引體向上也能做好幾組了,推手也能在同班的重量級選手面前多撐半分鐘了,體測成績也從勉強及格走向十分良好了,一切都讓我愈發篤定,老林肯定就是那個傳說的主角。
人世間的大恩大德莫過于二,一曰知遇,二為再造。身體的再造,當然也算得上是一種再造,見過了老林之后,我就再也沒為體測的事情發過愁,上課的時候便更加積極了些,一來二去,老林便也對我有了印象,走在路上主動和學生打招呼的老師極少,他算得上一個。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把鼻尖埋進熱氣里,用嘴吹吹撲面的白霧,皺皺眉頭,合上杯蓋,起立走到窗前,臉湊向玻璃外的世界。
“你們年輕人喜歡過陽歷,對吧?”他背對我,冷不丁問出這么一個問題。
窗外是深冬的正午,白茫茫的世界里,隱隱透著冬青的深綠,雪花迎風招展,簌簌落到一半,又被風卷起來,飛的比樓高,從窗臺下出現,一直飄到窗框的頂點,淡出視野,消失無蹤。
我合上手里的書:“您說什么?”
老林轉過身,仍舊是滿面紅光,保持著他課堂上的招牌式笑容:
“我說,你們年輕人,是不是喜歡過陽歷春節啊?”
“您說……元旦嗎?”
“對!對!是元旦,是元旦!就是今天!”他的臉上流露出些許的尷尬,須臾間又被上揚的嘴角掩蓋過去:“今早上我一起床,看見手機上不少學生昨晚上發的消息,你瞧,就是這些。”
他把手機點亮,放到我的面前,屏幕上是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頭的消息盡是在昨夜零點發布的跨年文案。
“一年到頭了嘛,大家興奮些,也是蠻正常的事情。”
“有時候真羨慕你們年輕人,雪里蹦蹦跳跳,生龍活虎,想吃什么吃什么,和火爐一樣,把自己燒得通紅,通宵倒也熬得住,動輒就是成宿不睡覺,天天守歲啊。”
“您也正年輕。”
“別,我哪能和你們并列,不服老是不行的。”
老林和我說,他的確不理解,為什么他身邊的年輕人喜歡把“年”這個概念拉到正月的大門外。在他的眼里,元旦只是個可有可無的時點,只有進了正月的門,再堪堪走出一遭,年的味道才能濃起來,守歲就更不用說了,只在除夕那夜守一次便足夠,十二月最后一天熬到零點,他覺得不可思議。
“家住哪里的?”他喝下茶杯里的第一口水。
“本地。”我微微一怔,接著合上筆帽,整理著椅子靠背上的大衣。
“哪里人啊?”
“也是本地。”
“就在青島啊?好哇,不用來回跑,就地過年,真的有福氣,家要住的遠,不說舟車勞頓,訂個票就要花不少心思。一學期到頭,偶爾想家,也回不去,你的話,出溜一下就是一個來回。”
老林說的沒錯,距離產生美,也產生同等質量的思念,思念積蓄久了,就有了故鄉這個詞,在大多數人心里,自己總會離家越來越遠,家逐漸會成為一個點,如同亙古不變的孤島。
在老林看來,我是幸運的,我生在青島,長在青島,幼兒園,中學,大學,沒離開青島半步。
活脫脫扎根在這里。
這是個臨海的城市,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區并入其中,體量已然算不得小,就算如此,海風一年四季都能拂過市里的街道,除去高新區從拔地而起到鱗次櫛比的大樓,還有紅磚綠瓦壘成的那些建筑,中山路老火車站前七八級淺淺的石頭臺階,天主教堂前斑駁的海報墻——大概因為我的童年在老城的岔路間度過,這些老物什才真的讓我印象深刻。
當然,這一切也唯獨青島有,它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和我對視,既不徜徉,也不漂流,路牌一樣佇立在那里。
對視結束后,我繼續在這座城市的身上走。
年復一年。
2聽朋友說
“你猜我今天碰見誰了?”
“我能猜得到才有鬼了。”Z哥跪在地上,繼續用全身的力氣壓著他那超大號的行李箱,整個箱子鼓鼓囊囊,他一個一米九的壯漢,跪在箱子蓋上,手死命拽著身下的拉鏈,箱子這輩子沒受過這種委屈,不斷發出吱吱嘎嘎的抗議聲。
“不難猜到的,你見過的,男的,姓雙木林的,拜托,答案都寫在我臉上了好嗎?”
“林俊杰啊?”
“你神經啊?”我笑罵道:“哪門子的風能把林俊杰吹到我們學校來啊,是老林啦,林燦!”
他停下手上的活,箱子蓋如釋重負,噗嗤一聲彈開。
“他還沒走啊?學校的人都要走干凈了,體育課不都老早就結束了嗎?”
“他今兒個值班,批體育理論的卷子,今兒元旦圖書館閉館不是?我到辦公樓的自習區占座,正好碰見他從樓上下來打水,見我冷的直打哆嗦,他很慷慨地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看書。”
“他還記得你啊?”
“何止記得,他把我名字都叫出來了,盛情難卻,我在體育組辦公室陪他坐了一上午。”
“這么好的機會,你沒和他再討教討教什么化勁的功夫啊?就他上學期,最后幾節課上輕輕一推,把比他高出一頭的胖胖推一個趔趄的那一下子,我是沒看明白奧。”
“討教?哦,他倒是和我討教了,只不過我沒回答上來。”
“得,我明白了,”Z沖我吐吐舌頭:“合著你幫他修了一上午電腦,沒修利索唄,說得那么隱晦干嘛。”
“屁,他問我們為什么喜歡提前過年。”
話一說出口,我心里暗暗叫一聲糟,這句話倒是精準無比地命中了Z哥的敏感區。
“這個,他得問問咱學校的管理層了。”果不其然,Z的聲音里透著難掩的激動。“老林最好去問問,是我們喜歡提前過年,還是學校的鬼安排讓我們被迫提前過年!”
他故意把“被迫”倆字說得很重,我自然知道他什么意思,也不敢多說一句。
今年學校的調休計劃確實蠻奇怪,原本的十一假期告吹之后,期末又突然通知,寒假要提前放一個星期,原本寒假長度本就在全國數二數三,這一下倒好,原本一月上旬的期末考試,直接排進了十二月底,期末復習時間被壓縮不少倒是其次,對Z哥這種家住在外省的同志,可謂晴天霹靂,原本早早訂下的車票,現在得退掉,退完了還不一定能訂到合適的,訂的不合適那就得等——他考完最后一科,在這足足憋了五天,眼睜睜看著舍友一個個跑掉。要不是還留下一個沒考完試的我,他真能背過氣去。
“不是假期的事啦……”我好歹唯唯諾諾地應了一句。“是元旦,老林說,他覺得你我這樣的年輕人有慶祝元旦的習慣是很新奇的事情,在他看來,我們好像在一月一號就把除夕的事情干完了。”
“啥叫除夕干的事啊?”
“熬到十二點。”我回答。
“好嘛,合著我們天天過元旦了。”
“也是,后半夜睡覺在我們看來真還是稀松平常的事。”
“話說回來,他不過元旦嘛?最起碼也得家人一起吃頓飯不是?”
“他自己說不。”
“也沒啥關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互相尊重就是啦。”他繼續開始忙活自己的大工程,剛剛從箱子里拿出幾件大衣,再用力一蓋,鎖扣發出清脆的咬合音。
“什么時候的車?”我問他。
“今晚上,十點半,到時候得麻煩個人,和我一起把這兩大箱子給送到宿舍樓底下。”
“我突然腿疼。”
“瞅你那出息,我能讓你白干啊?中午請你吃餃子好吧?”
“腿不疼了,要蝦仁的。”
“好好好。”
晚上,幫他托了兩個箱子下樓之后,我不顧他的勸阻,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一路送佛送到校門口。
等大巴車的時候,他問我,將來有什么打算啊。
——打算?
——是啊,大三了,不打算打算將來干什么?整個宿舍我都問完了,考研的,考公務員的,進企業的,進工廠的,繼承家業的,基本都齊了。
——我還沒想好,你呢?
——今上午我和我媽理論了一小時,我想考個行政管理的研究生,我媽想讓我趁早去考公務員,她說這是鐵飯碗,端的穩。
——考研好哇,但那得拼啊。
——沒辦法,不拼更難受啊。
送走了他,獨自一人晃蕩回宿舍,偌大的校園人影少了許多,雪不知什么時候停了,水泥地磚上覆蓋一層薄薄的白,踩上去,腳底不停發出雪塊碎裂的咯吱聲。
3 聽老爹說
“兒子,你將來有什么打算啊。”
倒車鏡里,老爹癱坐在后排,臉到脖子漲得通紅,兩眼惺忪無神地望著我的椅子背,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
“打算?我還沒想好。”
視野里的綠燈變紅,我緩緩在停止線前剎車。
“我和你說……要提前想,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老爹有的東西……我坦白了和你說,有些可以無償的給你,有些……需要你自己去爭取。”
老爹是生意人,自年底起,便開始打生意的局。所謂生意的局,就是來回送禮,和客戶吃飯,磋商,跑東跑西,上午見了A,下午去找B。
他說,生意人的飯局,是酒杯撐起來的。
寒假放得早,我便給他當司機,他不好喝酒,酒量當然也不大,每當喝醉之后,就變得比平常健談許多,喜歡說些怪話,不得不說,在他酩酊大醉后提出的所有問題里,這個倒是很正常的一個。
“爸,喝醉了就睡會吧,離家還遠呢。”
“不,我……沒喝醉,我正常的很,我希望你還是走正道,去學習,去生活……真到混的山窮水盡的地步,大不了咱爺倆一起做生意,你爹當時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他說話斷斷續續,話語里有酒精和煙草的氣味。
正月門里走了好幾步,就算沒了耳畔偶爾的那幾聲爆響,周圍的年味也濃了起來,路燈上大紅燈籠高高掛起,彩燈條在車道的上方羅織。
“和你說呀,做生意不容易,跑東跑西……上氣不接下氣,伺候客戶,他們請你喝酒,你還沒法拒絕……”他看我不回答,開始自言自語。“你要真想不出來將來做什么,那就和我一起做生意,你覺得咋樣?”
紅燈變綠,我慢慢踩下油門踏板,車子蠕動向前,匯入車流。
“你要想繼承我的公司,也沒問題,畢業之后,先收拾東西,去外面歷練一年,一年之后沒被社會踩死,公司就是你的,被踩死了,就死在外頭。”
我噗嗤一聲笑出來。
“爸,你今天真喝不少,快乖乖睡覺。”
“沒喝多,說了多少次,我真沒喝多!還有個問題我想征求你的意見,今年過年,想在哪邊過?還想和我一起……回老家嗎?”
“啊?不是每年都和你回爺爺家嗎?”
“遇見我之后,是不是就再也沒和你姥姥……和你姥爺他們,一起過大年?”
我沉默。
“今年不用和我回去了,你媽工作要求,就地過年,減少流動,你陪著她吧,多陪陪你姥姥他們,我也不能讓丈母娘說我偏心不是。”
“害,姥姥姥爺他們不會這么小氣啦。”
“人老了,容易多想,在他們多想之前,年輕小輩的行動必須得跟上,你懂嗎……就這么定了,你就當幫老爹忙了。”
不一會,沉睡的鼾聲從后座傳來。
4?聽老人說
陪老爹跑完最后一個客戶,置辦完全部的年貨,離除夕還剩下不到一周的時間。
雖然我在電話里再三強調,在家里乖乖等我,姥爺還是早早地等在樓下。
“你又不聽話,折騰什么啊。”
“不折騰,不折騰,我剛剛遛彎回來。”他從我懷里搶著接過東西,我說我自己來,自己來。
他在前面爬著樓,在我面前來了個平地摔,我攙他的手還沒伸出去,他卻搶先一步,用一個來人能做到的最快速度,重新站了起來。
我說,老天,你慢點。
他撣撣褲子上的塵土,微笑著說,沒事,沒事,別和你姥姥說這事。
姥姥倒是沒變樣,但姥爺變得比我印象里更加干瘦了些,也可能是許久不見的緣故,我并不想思考太多,他們只要硬朗,就是我的福分。
清早起床,陪他們打掃衛生,抹桌子,掃地,跳到窗框上去擦外頭的玻璃。
半年沒見,姥姥學會了自己剪窗花,選出幾個自認為得意的作品,讓我拿透明膠帶紙貼到大門外頭,我拿著尺子比著貼,不敢怠慢。
忙完幾件事,就停下來,吃吃水果,喝幾口熱騰騰的茶,他們把我聽不膩的那些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
晚飯吃的早,便隨他倆一同到樓下散步,一為消食,二也為增進鄰里的感情。小區不算大,各家的老人都在這個時間出來透風,大家一起圍著花壇兜圈子。
“嚯嚯嚯,大小伙子,還記得我不?”
“鄭伯,過年好。”
“是不是比以前又長高了?”
“劉奶奶您看花眼了,還是和以前一樣。”
每到這時候,大家便一起笑。
“大青年,過年好啊。”
“王奶奶過年好!王爺爺呢,沒和您一起下來?”
姥姥在身后拽了幾下我的帽兜,我正犯嘀咕,面前的老人笑著對我說:
“你王爺爺老了,腿腳不靈便,下不來了。”
“替我祝他新年快樂。”
走出幾步遠,姥姥對我說,你這孩子,哪壺不開提哪壺。
我剛想問她,剛剛拽我那一下,是什么意思。
恍惚間,我突然明白了。
回頭,王奶奶早已朝背對著我們的方向走出一段路,她的腳步聲很輕,路燈把老人的身影拉得老長。
5 敬他們
除夕晚上,年夜飯散場,姥爺不小心把酒灑到了褲子上,換衣服的時候,姥姥看到了他腿上的那塊淤青,逼問出實情后,一邊數落姥爺,一邊指責我,就不能好好扶著他。
姥爺不停地做鬼臉,不關孩子事,我覺得自己還年輕,這是代價。
我媽和我說,你多在這里住一段時間吧,陪陪他倆。
我把我表哥一家送到樓下,往回走的時候,褲袋里的手機振動了幾下,我點亮屏幕看。
太極臨班201 周四三四節
21:36
山山而川:孩子們,抱歉啦,我老糊涂,這個群早在半年之前就該解散的,我的疏忽讓它多留了一個學期,這學期,你們應當是沒有體育課啦,就算這樣,老師也希望你們不要把體育運動拋在腦后,平常走累了,要多休息,還記得太極拳怎么樣打的,記得要常練練,有什么想不開的,不開心的事,歡迎隨時聯系我。下課之后,路過我們上課的那片小樹林時,如果發現我在那里,記得來打個招呼。
山山而川:別忘了我這個老人啊,我會傷心的,除夕快樂。
該群聊已被解散
山山而川,是老林的微信名。
老爹丟過來一個蠻大的微信紅包,紅包封面上寫著,別忘了給你爺爺去個電話。
放下手機,周圍靜悄悄的,沒有鞭炮聲,夜幕中偶爾浮現幾個陌生的人影。下午又落過一段時間的小雪,樹杈上透著隱隱的白,抬頭見蒼穹深邃,藍黑深處生出點點深靛,星斗飄飄忽忽,在視野中游離,在凡塵間落地。
走到樓道口,某只流浪貓跟了上來,躡手躡腳躥到我背后,我轉過身來和它對視,它也不怕我,呆呆坐在我身前,喉嚨里發出陌生的音節。
喵,喵喵,喵喵喵。
謝謝,也祝你春節快樂呀。
我沖他揮揮手。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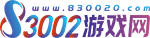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