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崔護在《題都城南莊》中,用短短四句詩抒發了濃郁的哀愁,睹物思人,卻物是人非,這恰是時間所具有的深沉力量,而這也正是《紫羅蘭永恒花園》系列作品中,隱含而又深刻的一大核心主題。伴隨著時間的編織,薇爾莉特跨越千萬里路遙,終于與基爾伯特成為眷屬,以劇場版中的勾指為約,為系列作品畫下了最溫柔而完滿的句號。讓我們將時間回調,從TV版出發,去探秘《紫羅蘭永恒花園》中,鐫刻在薇爾莉特身上的,時間的秘密。
時間:漫長
在作品中,體現在薇爾莉特身上最直接的時間特征便是其年齡的增長——從懵懂的幼女,逐漸成長為頗具氣質的青春少女,并且預示著她將要步入成人世界,擁有更多體驗,見識愈發廣闊的天地,這是眾所周知的人生趨勢,似乎并不值得特別說明,但其本身實際上暗含的是時間線性彈性延伸的超視域長度,沒有這樣的長度,就沒有薇爾莉特過往經歷的“歷史”、當下行進的“現實”以及未來無可預知的“可能”。
這樣解釋似乎不免有些抽象,但當我們將薇爾莉特與安兩人的經歷相結合,就能夠得到較好的感知。安的母親依托薇爾莉特給女兒安留下五十封信,在安生日之時寄給安,在信中,安的母親總是以安的年齡開頭,然后以對女兒的期待與想象作為內容,這就直接將“時間”與人生的階段性的“內容”相結合,而這樣一種巧妙的形式經由薇爾莉特親自書寫,便在薇爾莉特身上形成了雙重時間體驗:他人的時間經歷暗含著對自我時間經歷的隱喻和抽象,自己的時間經歷保證了他人時間經歷的完整性(關于此,劇場版中安的孫女黛西閱覽的祖母收藏的實在的信件就是證明),兩者相互交織,潛在地誘導著薇爾莉特的人生走向。
這其中,突出的自然是未來的走向(可能),即取得現實意義上與愛人相守而帶來的愛情完滿。安的時間經歷的預設代表了一種普遍性的狀態,實際上,除此之外,薇爾莉特在長期的代筆旅途中,經受了更多的愛情圓滿的特殊的時間經歷:劇院歌姬,王國公主,雪地士兵,從這些人物身上,薇爾莉特取得的隱秘的諭示是:愛情的精神圓滿,這些都與薇爾莉特現階段失去“愛人”后的精神追求構成無意中吻合。換言之,薇爾莉特等待、追尋基爾伯特少佐除了其內在對于少佐的現實性直接需求外,還有來自外部世界愛情體系對于薇爾莉特的深層驅動。
薇爾莉特對于”愛“的困惑也正是因此而得以形成。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容易發現與被認可的是“愛”對于薇爾莉特的積極效益,也就是薇爾莉特的那句標志性話語:“我稍微能夠理解一些‘愛’的含義了。”由此反推,則當然是薇爾莉特對于“愛“的經歷豐富其對于”愛“的理解度,這一理解本身固然沒有問題,然而并不全面。問題的關鍵,需要抓住“稍微”一詞上,而不是單純注目于“理解”之上。”稍微“,則正是薇爾莉特對于“愛”的理解困惑的直觀話語表達。之所以產生這種困惑,可以以時間角度,從兩個方面來進行理解。
一是從橫向上看,薇爾莉特經受的“愛”的種類復雜多樣。上述已經談及關于愛之中的愛情圓滿對于薇爾莉特的情感影響,但不能忽視的還有愛之中的親情,這一時間經歷對于薇爾莉特的影響同樣重要,主要涉及到三個人物:劇作家,觀星者,小兄長(尤里斯)。其具體內容不再贅述,可以明確的是,一旦糅合了親情與愛情兩種因素,愛的邊界概念就變得非常模糊了,這對于薇爾莉特來說是非常容易產生理解障礙的。
在與劇作家和觀星者的相處交談中,薇爾莉特都表達出了這種困惑。關于前者,父親失去女兒與自己失去少佐,在情感的直觀體驗上,確實存在鮮明的共同之處:痛苦。但少佐與自己之間是受養與被收養的關系,與父女之間的關系之中蘊含的痛苦,直觀上能夠明確是不同的,但同樣的情感,相似性又是難以找尋的;關于后者,薇爾莉特同樣不理解觀星少年失去父母產生的“寂寞”與自己失去少佐而產生的“寂寞”的關系,直觀相同而相似性難尋。那么少佐對于薇爾莉特所說的“愛”以及這之后薇爾莉特產生的情感究竟應當怎樣理解,對于薇爾莉特來說便愈發撲朔迷離。
這對薇爾莉特產生的潛在的思想影響是:對于“愛”的時間探索路程被無限延長。由于愛的種類繁雜,并且彼此之間的界限交叉模糊,“愛”的確切定義是什么,就變得不可知,這就是薇爾莉特求索“愛”的含義與”愛“本身的無限義之間存在的矛盾,換言之,愈是求解“愛”是什么,就愈發無法知曉“愛”是什么。因為”愛“本身不是一個理性概念,邏輯與符號不能夠對其規制完整明確的定義,它是需要感受而得以知曉的特別存在。薇爾莉特所說的“我稍微能夠理解一些‘愛’的含義了”,不是指憑借邏輯理解了“愛”的理性意義,而是依靠感受體會了“愛”的感性氛圍,而這樣一條路,是薇爾莉特窮極一生也無法走完的。
二是從縱向上看,薇爾莉特所經受的“愛”各自具有深刻的復雜性。這復雜性,其中一方面就是對于“愛”的表達的曲折性,與少佐對于薇爾莉特直抒胸臆的話語表達又存在明顯不同。這樣一種對于愛的表達方式,一方面使得愛的傳達在形式上被削弱,從表面上看缺乏感染力;另一方面,它通過造成意外效果,促使受事主體在追思中自主調動起超量級的情感記憶,“愛”的內容與意涵由此而又被極大充實并升華,沖擊力由此增強。
更具體來說,這種曲折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愛”訴諸于信件文字而不是話語,這是比較明顯的;二是不直接將自己的情感內容傳遞給對方(在其中包含著對于對方想要接近自己的一種無奈抗拒)而是委托中介(薇爾莉特),尤里斯與安的母親的情況皆是如此;三是情感生效的滯后性,信件內容的讀取與情感的發生,皆在與施事主體離開人世以后,因而對于其“愛”的表達,受事一方則沒有現實層面的反饋、回應渠道,而唯有將其轉化在精神上,無意識地使得情感多重反復地積累疊加,具體來說,也就是深沉長久地懷念,對于施事者的印象能夠被隨時、偶然地喚起,進而形成一種近乎永恒的記憶。
那么,這樣一種曲折表達的緣由,就十分值得探究。依然以尤里斯和安的母親為例,他們在曲折地實現自己對于親近之人“愛”地表達時,首先營建起與親近之人的疏離——抗拒見面與談話,這樣的回避中,又具有相同點與不同點。
相同點一是在于因時日無多而擔心造成遺憾,二是希望避免自我傷口的擴張反而抑制了對于“愛”的表達的欲求:尤里斯抗拒與父母以及弟弟見面,是因為這會讓他反復看到自己因為弟弟而”失愛“的心理現實,從而容易激起嫉妒與厭惡的情感火花;不愿意與好友琉卡見面,則是害怕向他直接暴露自身病體的羸弱,加重對于自我的嫌惡以及對于這段友情在現實中難以避免地走向死亡的痛苦體驗,進而真正排斥琉卡;安的母親抗拒與安相見,是因為不愿意因為女兒的介入,而讓自身反復回想起自己(讓人代筆)書寫的是近乎“遺書”的凄冷現實,是必將與心愛之人天人兩隔的悲哀,就此才能夠載著美好的回憶安然離開。從這一點上來說,曲折,是一種自私的體現。
不同點在于,一是尤里斯是兒子對于父母(和弟弟)的愛,動機中含有微妙的羞澀感,安的母親是母親對于女兒的愛,動機中則傾注了精神守護的期盼(例如,在其中一封信中,安的母親對安說“媽媽永遠愛著安妮”);二是尤里斯不愿因自己的訴求而又剝奪了弟弟享受父母之愛的權利,也就是無法任性地“撒嬌”,是對自我本性的壓迫而成全他人;安的母親則是不愿意讓女兒提前感受失去雙親的沉重孤獨,想要在最后剩余的時光用盡殘力保護安作為一個孩子本應享受的哪怕只多一分鐘的美好童年。從這一點上來說,曲折,又是一種無私的體現。
利己利他的悖反統一性,是“愛”的曲折之復雜性的核心要素。這統一性正在于:利他是利己實現的目的,利己是利他實現的前提,這是現實世界的愛,并不是理想化的純粹,即奉獻的利他。這其中包含著的“利己”的“雜質”如何與利他能夠和諧地結合,這才是對于示愛主體與觀愛主體最為復雜的難題,特別是對于薇爾莉特這一有意識探求愛的本質的人來說,則顯得更為復雜。
在替安的母親為安寫信之時,表面上看,對于薇爾莉特自己來說,她出于對職業操守的嚴守,對于安的母親(也就是服務對象)隱私秘密的保護請求,對安閉口不談,但在其內心的背面,薇爾莉特以職業行為完成了一次心理升華的過程,也就是在潛意識之中知曉保守安的母親的秘密,是對于安的母親愛的傳達的最好而最無奈的方式。薇爾莉特冷靜地懷抱著向自己撲來的悲痛不已的安,又在自己回顧這份不同尋常的代筆時淚如泉涌,前后的鮮明反差與轉折,正是對于這一”愛“的體會達到深刻的表現。
具體來說,即薇爾莉特并非不是在一開始就知曉安的母親的意圖,但在全程服務的過程中,薇爾莉特也并沒有在外在呈現出強烈的情感波動,直到她抱住安的時候,情緒都始終在如風暴般的聚集之中。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薇爾莉特甚至不必要付出特別的努力來實現情感抑制,并且實際上,這一情感是自然的自動地自我壓抑,是一種無法控制但自然實現的“忍耐”;在之后,薇爾莉特進行過程回溯時,想要抑制自我情感,反而卻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了了,以流淚的極強的外在形勢體現了其情感的波動,形成風暴。這就顯示出曲折的愛的獨特效果:在感知與體會之間,勢必有一個漫長的沉淀期,在你能夠感受的時候,難以體會,在你已經體會時,感受的形式也就自然沉默地消散,“愛”由此成為你的一部分。
在這時,薇爾莉特體會到的便是這曲折之愛的利他性:不僅存在愛的發出者對于愛的直接接收者產生影響,對于薇爾莉特這樣的第三方觀察者,同樣也產生了作用。并且,這樣的利他性,即愛的純粹的部分,只能是建立在愛的利己性的基礎之上的。沒有這樣的利己性,就無法產生”遮蔽的隱秘“,“隱蔽-揭示(自白)-回溯-構型”這一心理機制也無法發生。一旦將這種體驗對象化,也就是所謂“構型”后,在現階段就有了實相憑借的情感體驗,延長了這一階段的心理時間體驗;并且在之后的時間段之中,又會隨時隨機地產生會回溯的機會,每一次回溯,又都延長彼階段的時間體驗,從而使得薇爾莉特的縱向的時間體驗具有多層次的豐富性,這造成的結果不是單純的再知曉,而是溫故知新,從而不斷積累起關于愛的認知。
上述第二點是從薇爾莉特關照客體的角度說明薇爾莉特縱向時間體驗漫長性的形成,但實際上,薇爾莉特也常常關照自我而進行回溯,客觀上延長自我時間體驗,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依靠實物,睹物思人,而進行回憶;二是口述概念,對概念進行無意識追究。
第一點,主要表現在薇爾莉特胸前的綠寶石胸針,也就是少佐在薇爾莉特幼年時送給她的禮物。薇爾莉特一旦意識到胸針,便會想起少佐,這種心理機制的產生不是抽象的。薇爾莉特之所以會因物思人,根本原因就在于相似性:即綠寶石的形色與少佐眼瞳的對應,以隱喻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固定的無意識。
而致使回溯這一行為產生的觸發原因則是失去。失去,在心理層面與獲得緊密對應,求而不得,反饋的階段性而產生的不完整性,反而激起薇爾莉特不斷回溯,具體來說,也就是因為無法見到少佐,反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少佐”。而一旦開始思念(回溯),時間定點必定向前回調,具體來說,主要定格在兩處時間點:一是少佐為薇爾莉特安上胸針(短暫的和平期),和少佐對薇爾莉告白后與其霎時分別(焦灼的戰爭期)。
這兩處時間點選擇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前者是回溯的對象實體實現最初形成,后者是”失去“的最初開始。同時,這其中還具有回憶色彩的暗示,并以彼時的大環境作為發生器:前者渲染出亮麗的色彩,呈現出彼此關系的和諧性;后者渲染出晦暗的色彩,呈現出彼此關系的震蕩性。在這一反差的映照下,困惑也便產生:美好是真實的,但美好又失去了。從現實邏輯上思考,歷史不會虛無;但從心理現實關照,歷史便具備了假設的可能。而這兩種思維模式總是結合起來的,于是,求證——這一心理需求便產生了。
薇爾莉特行為的核心線索就是尋求愛的本質,這一啟發是由少佐的對于薇爾莉特的口述而產生的,不是單純的想,而是做,即行動。看似往前推移,實則向后反證,換言之,時間物理意義的向前是客觀的,薇爾莉特內心的時間卻是在瞬間實現永恒的或是不斷后退的。并且,這里的后退,一方面是指時間在線條上收縮,另一方面是指時間體驗的加深,兩者不是相互隔絕而是相互交織的。
通過求索與求證,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時間通道就由此而被疏通,關于少佐的面貌以及記憶的真實性便逐漸被確立、完善與定型,而其互通的媒介,便是薇爾莉特受贈于少佐的胸針。這一物件具是以現存實體的存在作為記憶真實的第一驗證物,具有現在與過去雙重時間的見證性。惟其實際存在,其與主體的關系形成的過程才絕不可能是曖昧混沌的,只是現在與過往之間存在一層遮蔽,費勁心力揭下面紗的回溯,才最富于時間體驗。
第二點,核心表現為對于孤兒概念的意識。孤兒意識,成為薇爾莉特內心的核心創傷。關于孤兒這一說法,薇爾莉特自述的情況極為少見。在參與一次天文臺的代筆委托中,薇爾莉特說出自己是“孤兒”。在說出“孤兒”二字時,薇爾莉特便在瞬間完成了一次時間回溯。因為孤兒這一概念,天然包含著一個時間概念——被拋棄(有意或無奈)與拋棄的意識之間,至少存在一個不容易被察覺的短暫瞬間,隨著時間增長,這一瞬間體驗就被自然延長了。
對于薇爾莉特來說,孤兒的遠期感知是,自己被父母遺棄,這是血緣上的,也是最為原始的概念(在天文臺協助工作時曾提及);二近期感知則是,自己與少佐的分別,這就是屬于衍生的概念,即被賦予自我生命之人拋棄,成為兩次孤兒意識的共同特征。雖然少佐和薇爾莉特的父母不具備任何直接聯系,但對于少佐的回憶必然會讓薇爾莉特回憶起自己的父母,也就是進行時間回溯的跳躍。不能將薇爾莉特的兩次時間回溯統一,因為雖然父母與少佐都是賦予薇爾莉特生命的人,但彼此仍然有時間順序的絕對隔斷性。
這一隔斷就是生與養的割裂。首先,薇爾莉特被遺棄而成為孤兒時,其父母,無論出于何種緣由,客觀上都將對于薇爾莉特的生與養割裂開來,從而造成薇爾莉特生活的殘缺;其次,對于上述薇爾莉特父母的生養割裂,核心也就歸納為“生”,而“養”,則由少佐承接,也就是說生與養本應統一的行為,卻被拆分給本無關系的兩方主體。換言之,生養從行為先后變異為主體先后,這一實相化的更改,便主動造成了時間體驗的斷層,即孤兒這一概念必然是讓薇爾莉特從遠期回溯跳轉到近期回溯,并回歸到“此時”的時間段。換言之,孤兒意識的存在,又造成了薇爾莉特對于時間連續性的混沌,在不真實的情況之中,時間的線條長度又被無限延長。
這是從回溯的跳躍性角度來分析。現在將視角回歸至孤兒本身這一概念上來。孤兒對于薇爾莉特來說,有一個界定的時間段,即失去父母之后到重遇少佐之前。在這一時間段中,薇爾莉特對于父母的追尋是迷失的,進一步說,薇爾莉特對于自我生命誕生、時間開始的概念是模糊的;另一邊,失去少佐而幾乎喪失重遇的可能,這使得薇爾莉特對于生命結束的確證在心理現實上感到混沌。
于是,在以被拋棄為核心表征的感知籠罩中,薇爾莉特在孤兒期間喪失了對于時間完整性的把握,即起始與終點的終極曖昧,幾乎喪失求解的可能。換言之,薇爾莉特在這一期間生活狀態與時間體驗是鮮明的失重,處在漂浮的狀態之中。這與其有明確的追尋目標的客觀現實并不矛盾,因為心理現實與邏輯現實往往存在不平衡性,或者不如說是目標的明確性使得內心的空洞感愈發鮮明。
除了孤兒意識之外,薇爾莉特對于概念審視而產生的時間體驗的,還有罪人意識。這一意識造成的時間體驗最為特殊,它使得時間聚焦為一個點,沒有延展性,卻無限空洞,并使得薇爾莉特被囚禁于這一時間異點之中,在時間體驗上構造出瞬間無窮的效果。
對于薇爾莉特罪人意識的喚醒,從外部環境看,少佐的哥哥布甘比利亞大佐是核心人物。在薇爾莉特成為脫離戰爭,離開少佐,成為代筆人偶之后,布甘比利亞對薇爾莉特說了這樣一句話:“用你這沾滿鮮血的雙手......寫替人結緣的書信?”并且,在于霍金斯中佐的對話后,薇爾莉特自己談及罪孽時,以確定的姿態強調,“我在燃燒(罪火)......因為自己做過的事。”
從自身來看,薇爾莉特的義肢是其作為罪孽制造的第一見證實體。在每一次為人代筆之前,薇爾莉特脫下手套,露出義肢時,對方都會驚訝,于是薇爾莉特就會解釋這是戰爭的緣故。這是一個大的方面。從私人角度來看,義肢的存在還提醒著其對于少佐的罪孽:因為失去雙手,所以在最后的關頭無法用手而只能用牙齒拖拽身處險境的少佐,并且失敗,于是,養之恩就此而(在彼時的心理中)無法回報,成為沉重的遺憾。薇爾莉特通過代筆傳信洗刷自己的罪孽,但是無法洗凈,因為義肢不同于其他物件,它在現實中是與自身的肉體合二為一的,換言之,罪孽是與自身始終捆綁著的,這就像少佐失去一只臂膀,對于戰爭的話題便最為敏感。
罪孽成為薇爾莉特一生無法走出的圍墻,她只能在其中開掘、創造出更多價值,而無法逾越。存在于薇爾莉特自身及其周邊的,是現實的各類眼目,從義肢到胸針,再到布甘比利亞,薇爾莉特沒有回避的可能。并且在一些特定情況下,薇爾莉特還會以行動的方式折射出這樣的心理困境。
例如,在一次為少佐母親掃墓后,薇爾莉特遺落了一根發帶,當布甘比利亞想要拿出交給薇爾莉特時,薇爾莉特誤以為是危險行為預警,便迅速出手將布甘比利亞的手制住,但在誤會澄清后,又表示歉意。在那時,薇爾莉特無疑已經具有相當深刻的情感體驗與積累,心靈也得到了極大的洗煉,但應對戰爭培養出的后天性條件反射依然沒有去除,它時刻提醒著薇爾莉特她是戰爭培養出的人,薇爾莉特也正是回應了這樣的提醒,才會產生相應的動作。“即使強烈祈愿,也有無法實現的愿望”,這句薇爾莉特對于少佐思念的告白,完全可以用來說明薇爾莉特包括罪人意識在內的,諸多無法突破的心理的時間屏障。
求愛與贖罪,都在主觀上造成主體內心時間的無限延長性,這是共同點,但兩者也具有不同之處。求愛所帶來的時間的延長效果,是一種溫和的狀態,這與其遭遇的愛的冷暖色彩和求愛的過程難易無關,因為它們本質上都是對薇爾莉特給予心靈滋養,“缺失”的彌補,帶來的是滿足感;贖罪則相反,必然是一種嚴酷的狀態,它不是彌補缺失,而是削減負擔——收獲的無限期進行勢必比負擔的無限期承擔在心理上更容易承擔。
然而,薇爾莉特之所以能夠承擔與堅持,原因在于求愛與贖罪并不是完全相互隔絕的。求愛的無意識層面的效果即贖罪,即以代筆的方式削減他者的精神負擔。在他者身上,薇爾莉特能夠體會到因為各種原因而使得愛不能夠實現的困境,由此而產生的缺憾構成了罪感,其躑躅不前的困窘姿態也就構成了罪的樸素原型。這樣一來,他者與薇爾莉特自身就形成了一種映射關系——自我的贖罪是曖昧的,但是寄托于他人,贖罪的意識即使模糊,但行為便清晰明了。
更進一步來說,求愛是一種顯著行進的過程,是動態的無窮,但是對于薇爾莉特來說,贖罪則偏向一個定點,是靜態的永恒,前者更容易實現持續性的諦觀,從這一點上來說,求愛的時間體驗對于贖罪的時間體驗存在一定的障蔽性。但這障蔽不是一種“覆蓋”,而是一種若隱若現的包裹。因這“包裹”的存在,被包裹的“內部”才能夠被感知——不能及不會使其消失,而是以間接的方式保留,以“觸發”的方式提醒(布甘比利亞:“用你這沾滿鮮血的雙手......寫替人結緣的書信?”及其現實語境)。在內部的調和中保持主體精神意志的持續性,進而確保其承受時間的漫長,這就是時間與薇爾莉特的糾纏,但本質上——顯而易見——薇爾莉特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被支配的從屬性,成為薇爾莉特時間體驗漫長的整體上的根本原因。
面對時間所制造的綿長困境,薇爾莉特在相當長的生命階段是以有限的時間來對抗的,但其與時間的關系沒有發生根本轉換。直到最后,薇爾莉特將自己化為時間,或者說將自己融入時間,成為一種無限,這才實現了與時間關系的根本改換。具體來說,薇爾莉特在最后選擇了為一座小島上的郵政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從而讓自我成為了記憶。
小島郵政事業的良好發展與世代延續,表面上看是薇爾莉特的職業功效的一種后效,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則是薇爾莉特將贖罪化為永恒進行的狀態——不但澤福后代,更構建歷史,使得“此處”因為薇爾莉特的存在而形成了一種集體記憶,并具有了時間所特有的深度與長度的永恒價值——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層面。
具體而言,“此處”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巡游觀光與紀念價值,薇爾莉特作為舊時代的手記人偶具有歷史考證的活化石作用,安的外孫女黛西,正是通過小島巡游,才得以更加親密地接觸手記人偶的歷史,并重新體驗外祖母的那段心路歷程,進而實現自我與家庭的和解。薇爾莉特的存在,巧妙地將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相結合,并在此基礎上,能夠使得包括黛西在內的諸多人物,在知曉“歷史真實”后,實現對于舊我的超越,這也就代表了薇爾莉特求愛這一時間動作的蛻變——由自動到使動,即促使他人求愛,在回溯與追求中,各自實現時間體驗的無限延展,帶有一種微妙的同化色彩。
總而言之,薇爾莉特自身包含的時間的漫長性,即體現為為最基礎的形容更換,也體現為將自我化為時間而實現永恒。在時間的漫長性中,薇爾莉特的兩大核心行為體現為求愛與贖罪,前者主要表現為追尋(未來性),后者主要表現為審查(現在性),并且統括兩者的,又是回溯(過去性),三者又相互交織,形成了薇爾莉特內部時間漫長特質的多層次多樣化的復雜性,這也是薇爾莉特三大時間特質中,最為核心、突出的特質。它將薇爾莉特的生命在體驗層面延伸到了接近于無窮的狀態,從而使其更完整地體驗了特質獨立的“自我”。
時間:欺騙
薇爾莉特的成長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認知更新的過程,從整體上看,即從身份的無認知,到戰爭工具再到個體的人本身。在這表面的樂觀下,薇爾莉特承受的是戲弄性的時間負擔,即每一次的身份認知不是主動求索的收獲,而是延滯性的被認知,換言之,身份的確認不主要受制于薇爾莉特其主體自身的意志,她只能是承受身份。在每一次認知模糊中與對前一次身份認知的拋棄中,自我身份——承載時間的容器——便顯示出虛假性。進一步來說,這種虛假感產生的實質,是在于被拋棄之身份損耗了冗余時間。被損耗的時間于時間自身無傷,卻嚴重消磨了主體的精神。
這樣一種無認知性,具有現實緣由,在身份的無認知階段中,主要受制大環境的境況。薇爾莉特的”誕生時間“與“戰爭時間”以不可捉摸的力量結合在一起,薇爾莉特的家庭狀況自此而走向不可知——她以非自主的姿態成為了遺落在南部戰區的“孤兒”。在這樣的情況下,薇爾莉特與父母分別,歸宿走向迷失,兩者相結合,造成薇爾莉特被剝離于自我時間之外,換言之,薇爾莉特自我被抽為真空,其缺少對于自我存在的感知。
在這種狀態下,薇爾莉特的游離和落定基本上是隨機的,時間形態表現為無序的混沌,這混沌之中正蟄伏著薇爾莉特時間的真相——自我的時間。然而要想接觸到自我的時間,前提是對于自我時間的無認知要能夠得以認知,然而這對于彼時的薇爾莉特是無從實現的。薇爾莉特家庭所在的生存環境的動蕩無憑,構成的是認知的自身的不可靠性。在自我與認知之間,形成了距離,這道距離的實質是徒勞感與惶惑感。由此,薇爾莉特對于認知的無意識疏離,便構成了其元認知系統的癱瘓。
因此,當只有重新回歸一個新的穩定環境系統之中時,薇爾莉特才具有實現認知的回歸的可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所謂“穩定”,不完全包含“溫柔”一類的積極因素,而只在于其“穩定”本身。之后薇爾莉特身處的軍營生活,充滿各種危險與殘酷,但是由于少佐的照顧以及軍紀的存在,“穩定”,仍然是客觀的。雖然薇爾莉特重新進入到一個“穩定”的軍營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認知就得以完全回歸。如前文所言,對于認知的徒勞感,使得薇爾莉特在重新掌握認知時,具有一種無意識的“晨起效應“,即倦怠與推就的掌握,并且,“認知”不單純具有“知曉”,而且指向“洞察”,這兩者注定薇爾莉特的認知回歸必然具有階段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戰爭工具的認識階段中,是由于薇爾莉特的受教育水平不足,主要表現為判斷和表達能力的不完整性。在判斷方面,薇爾莉特欠缺對于“反對”的認知,這來源于軍隊命令造成的思維慣性,越過對于主體正規的思辨培養而直接灌輸無原則的同一,這勢必造成絕對服從,將自我完全他屬化,從而造成自我主體意識的泯滅。表面上,薇爾莉特不斷向少佐表達自己是“少佐的工具”,但這樣一種認知,實際上無限接近于“認識”,即”確認“本身,對于概念的”所指“沒有真正“理解”,即彼時薇爾莉特并不知曉人成為他人的工具是意味著自我獨立尊嚴的喪失。
在“反對”的缺失中,薇爾莉特喪失了屬于自我的時間,而是將他人的時間作為自我的時間進行寄生,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時間體驗。具體而言,即薇爾莉特沒有在思考自我需求的狀況下進行行為,于是也就沒有依靠自我進行時間的推動。
只是因為判斷殘缺還不足以使得薇爾莉特喪失自我的時間,表達的殘缺也是重要原因,并且,表達的殘缺是與判斷的殘缺緊密相關的。在被他屬化的進程中,薇爾莉特喪失自我思考和思考自我的能力,于是進而喪失了完整的表達能力。薇爾莉特的表達,是接近于機械的反饋,而不是完整的對于自我訴求的闡述,因為其自我訴求已經被壓抑至難以察覺的境地。
在表達殘缺后,薇爾莉特與四周人物就缺失了自然的互動關系。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無論他者(特別指軍營之中)在何種狀況下表達對于自己的行動請求,薇爾莉特均以回復命令式的話語模式回應,例如:少佐讓薇爾莉特選擇自己喜歡的禮物,薇爾莉特誤以為這是命令,并詢問如何選擇;二是當他者自然對自我施加某種一般的社會行為時,薇爾莉特無法正常回應,例如當少佐為薇爾莉特戴上綠寶石胸針時,薇爾莉特沒能表現出一般的青春期少女的驚喜之情,反而微微抬頭,眼神表現出惶惑之感。
在這樣的極端對立的表達模式之中,薇爾莉特既難以完整接收他者傳達的信息,也無法正確表達自我的想法,從而使得自我將自我困于時間的泥淖,陷入一種無救的境地中。假若四周的環境沒有發生變化,那么薇爾莉特必然就要繼續進行非自然的人際互動,周而復始地強化自我的他屬性,從而無法逃脫屬于他人的時間。只是在戰爭結束,少佐消失,霍金斯出現,環境出現根本變化時,薇爾莉特才能夠具有逐漸脫離對于舊有體系的依附,也就是說,這時薇爾莉特又將走入一個新的“穩定的環境系統”——C·H郵政公司——任職自動手記人偶,從事代筆工作。
在這一階段薇爾莉特取得的重要成果是能夠表達出自己”不再是少佐的工具“這一觀點。從表面上看,這便是其人格獨立的標志,但實際上以此來作為判斷,尚還有所欠缺。薇爾莉特能夠實現這樣的表達,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來源于其自我探索的結果,而是少佐的啟迪:“你將不再是工具,而將成為如(紫羅蘭【violet】)這一名字一樣的人。”薇爾莉特的表達,實際上是承接了“少佐”的這樣一種“期待”,其構成的精神導航指引薇爾莉特成為“不再是工具”的人。也就是說,即使薇爾莉特在表面上看能夠意識到自我存在的獨立特質,但這一特質,仍然可以說是是“被賦予”的,是被預設了的導向的結果,不是真正依靠自我對于自我獨立價值的判斷而實現的人格覺醒。
在這一階段,與少佐的重新見面,是對于薇爾莉特來說的一個終極目標。貫穿其中的三大核心行為——回溯,審查以及追尋都是以少佐為核心展開,這本身其實仍舊反映出對于少佐的依附性的一種殘留,薇爾莉特的時間,此時還不能說是完全屬于她。只有當薇爾莉特取消了對于少佐在自我心理中的終極地位,在少佐與薇爾莉特自我所需求的他物的雙趨沖突中能夠選擇后者時,才能說薇爾莉特人格開始獨立、覺醒。
如果將這一“他物”具體定義的話,應當是手記人偶的職業行為。換言之,即薇爾莉特身為自動手記人偶,對于自我職業的深刻認識與嚴格尊重而生發出的行為。隨著工作經驗的豐富,薇爾莉特逐漸從代筆這一概念本身中跳脫出來,對于代筆所代表的對于“心意”的傳達和“愿望”的實現有了靈活的把握。早在艾麗卡作為手記人偶與薇爾莉特共事時,前者就表達出自己對于成為劇作家的渴望。在之后薇爾莉特幫助劇作家奧斯卡解決心事后,順水推舟,讓艾麗卡到奧斯卡處作學徒。
這表明了薇爾莉特所從事之職業的一種神圣性:不是一種機械的活動,而能夠切實實現對于職業者人格、生活的充盈。這一前奏能夠幫助我們窺見薇爾莉特之于自我職業的深刻認同,進一步說,是將職業自我化,兩者渾然一體,形成了一種崇高的境界。
所以,在之后薇爾莉特與少佐只有一墻之隔而不得見,卻沒有就此沉淪“此處”,而是留下書信,決然離開。這一行為也就顯得非常自然。從具體的一方面來看,關于尤里斯的代筆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出于職業使命感,不得不離開;從宏觀的一面來看,萊頓保有自我職業的整個系統,不回到那里,在彼時,便難以延續自我的職業生命。也就是說,直到此時,薇爾莉特的自我人格才能夠稱得上覺醒與獨立,至少說是借助這一行為具體表現出來。這一人格覺醒與獨立不是抽象的,它正表現為薇爾莉特對于自我職業深刻持久的認同感與使命感。
薇爾莉特選擇辭去C·H郵政公司的職務而專門前往少佐所在的偏僻小島開展新的郵政服務,這一選擇的堅決性,對于少佐的愛只是極小一部分因素,更重要的在于其職業自由意識的顯現:不是“被賦予”身份,而是主動賦予自我身份;不是被動等待環境變化,而是主動更換環境;不是囚禁于自我的情感,而是有意識地奉獻自我。能夠離開原本的舒適圈而扎根僻壤,這反映出薇爾莉特之于少佐的愛不再是一種虛幻飄渺之物,而升華為相守、互助與奉獻,換言之,兩人之間的愛不單純是屬于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小島的社會生態而存在,為其輸出自身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薇爾莉特超越了自我狹小的個體,而化身為整個群體,這才是薇爾莉特最本質、最神圣的身份。
直到此時,才能說薇爾莉特實現了對于自我時間的追回,在混沌之中埋藏的,其實正是薇爾莉特揭開混沌所發現的自我的根本身份。但是,正如薇爾莉特所具有的“時間的漫長”這一特質之中“隱秘-回溯”機制一般,為了實現對于自我根本身份的發現,就需要先無法發現自我的根本身份,于是由此而在無意識中承擔起對此實現的義務。這就是屬于薇爾莉特“時間的欺騙”這一時間特質的第一方面。
以上所論述的關于薇爾莉特“時間的欺騙”,是從整體的、線性的方向推進的,為了說明薇爾莉特“時間的欺騙”的層次性,則有必要從更加具體的橫截面展開探討。在微觀層面上,對于“時間的欺騙”的分析,可以從人物的謊言出發進行建構。
①第一次謊言:薇爾莉特戰后修養于醫院時,霍金斯中佐對其“謊稱”少佐仍然存活,保存了其生活下去的希望。
②第二次謊言:薇爾莉特成為手記人偶從霍金斯中佐處獲悉少佐“死去”的消息,“墓碑”、戰場遺址的存在篤定了其對于這一“事實”的認定。
③第三次謊言:薇爾莉特知曉少佐存活,卻被少佐拒于一門之外,無奈之下只有離開。
人物的謊言與“時間的欺騙”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建構關系呢?這里需要說明一個概念,即“時間分軌”。將一個原始的時間(基本時間)看作一段軌道,在軌道行進至某處時,需要進行分軌操作,由此而變化為兩條各自延申的軌道,不同的軌道自然導向不同的方向,這也就對應著時間分化為兩條不同的通道,每一條通道對應主體行為的不同及不同結果。而在道岔處發揮作用的裝置,就是“謊言”。換言之,謊言使得薇爾莉特的可能被不斷中斷與更換。對應上述三次主要的謊言,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薇爾莉特與少佐在戰場上分別后直到住院時霍金斯前來探望她之前的這段時間,是薇爾莉特的“基本時間”。這一時間的直接延伸,是薇爾莉特知曉少佐“死亡”(下落不明)的事實(通道),進而崩潰(導向)。霍金斯的“謊言”,使得這一直接延伸被中斷,只從薇爾莉特的主觀層面來說,她便因此而墜入幻想鄉之中。因為堅信少佐存活,所以本應當在這一階段產生的心理動蕩,沒有在薇爾莉特身上發生。并且,這一段時間,也就自然過渡為薇爾莉特的新的“基本時間”。
這一“基本時間”自然延伸的通道和導向與第一次“基本時間”的相反。但必須說明的是,霍金斯的謊言促使時間分軌的結果雖然是將薇爾莉特推向知曉少佐“死亡”的事實上來,但這不能將其視為回到第一基本時間的自然延伸上。在第二基本時間的分軌中,薇爾莉特相較于第一次而言,多經歷了“確認的崩潰”。第一基本時間的自然延伸中,薇爾莉特至多存在“自我確認”,而第二基本時間的分軌前,薇爾莉特存在“自我確認”和“他者確認”的雙重錯誤認識的疊加,這里來自包括霍金斯中佐在內的“他者確認”,不是與“自我確認”相隔絕的,而是對薇爾莉特”自我確認“的再確認,心理現實的真實這才得以建構。
在心理現實的真實的瓦解中,薇爾莉特強烈感知到”謊言“的存在,本應提前到來的時間被延滯至今,而且發生了一種變異(確認的崩潰)。但同時,薇爾莉特的心理現實的真實沒有完全瓦解,這又是由于“自我確認”和“他者確認”的相結合的“確認的重構”。在薇爾莉特處,對于不愿接受的現實的抗拒形成了“自我確認”的樸素原型,即懷有少佐存活的渺茫信念;在他者,少佐的失蹤,并不與“死亡”相對等,而“死亡”只是成為驅散混沌、確定現實的一種便捷措辭,這其中沒有對于“死亡”的“確認”,這也就為薇爾莉特的“自我確認”又進行了間接的再確認。從“崩潰”到“重構”,是一個短暫但龐大的更換過程。
順著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基本時間”也隨之更新,即“認為少佐存活”到被少佐拒絕見面之前這一段時間。在此處分軌中,直接延續是與少佐見面,分軌導向是沒能與少佐見面,延續之前的分軌邏輯,薇爾莉特被導向后者,而道岔功能的發生裝置則是少佐的謊言——不能見面。但與之前分軌裝置不同的是,這里少佐的謊言起到了連鎖的兩段分軌的作用。第二段分軌的直接延續是薇爾莉特獨自生活,分軌導向是與少佐真正見面——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分軌裝置是什么呢?
按直觀而言,這一裝置必然是與少佐的謊言有關的謊言。先回到具體的情境中:薇爾莉特因為在歸船上聽到少佐對自己名字的呼喊,然后跳入海中游向少佐與之相見。在這一情景之中,引導走向不是謊言,而是謊言的背面,即“真實”,即對于之前的分軌裝置是顛倒的。從反面來看,若以謊言為分軌裝置,則其直接延續和分軌導向便無法存在,因為不存在在“沒能見面”的前提下能夠實現“見面”的直接延續的邏輯悖論。這是作為基礎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這一“真實”是與第一個謊言的啟動效果相反,從而在整體上實現一個閉環,中止時間的無限分軌,也就是說為了中斷邏輯進行,就必須要反邏輯。落實到具體的情境具體的主體上,心理動機就是樸素的對于謊言的反感,行為表現就是結束分隔——因為分隔,在信息不通的前提下,謊言才得以誕生,人物時間路徑的更換才不斷進行,精神能量也在變途的無意識與識途的意識轉換中不斷折損,反邏輯簡言之即自衛的本能驅動。
在分-合閉環后,薇爾莉特其自身蘊含的“時間的欺騙”,也就暫時完結。“時間的欺騙”,其本質正是使得薇爾莉特這一主體在行進中產生被不可知力量操縱的迷失感與恍惚感。必須首先具有迷霧混沌,然后薇爾莉特才能置身其中找尋自己的時間。尋找到屬于自我的某種“本源”,然后確證獨立的自我個體,這是人都具有的一種動力核,無論是否能夠意識。“時間的欺騙”的存在,不是對于薇爾莉特的惡作劇,或是一種具有陷阱特質的抽象的詭譎,而正是要使她成為她自己,使她自己得以知曉并發現自己的“存在”。
時間:報恩
薇爾莉特在某種能力的掌握中,總是會呈現出異于同級人物的“精通性”,在更短的時間內,就能夠實現更快的技巧熟練。這一現象,主要表現在其作戰和代筆兩項工作的能力掌握上。不能脫離具體的情境抽象地看待薇爾莉特的非同尋常的能力,而需要注意其能力掌握的階段狀況。這兩次能力的掌握都生長于“時間的喪失”之后。
作戰能力的習得,是在其成為孤兒(第一步”時間的喪失“),受制于他人的控制(第二步“時間的喪失”)后實現的。因為自我時間的喪失,薇爾莉特具有獲得了聚焦于“對象”的強大專注力,以及客觀上獲得了在“對象”身上付出的大量實踐機會。代筆能力的習得原理大致相同。
這兩項能力,表面上看是沒有關聯的,但是在實際情況中,往往共同發揮作用。作戰能力,其中具體的一方面表現就是身體的運動機能。例如,在為劇作家奧斯卡代筆的過程中,為回應其無心的請求,薇爾莉特撐傘飛躍湖面,這一爆發性的跳躍能力是訓練的結果,沒有這一動作的實現,后續的代筆工作很難深入進行及完美完成。
也就是說,兩次能力的習得不是各自提供了一個孤立的技能本身,而是具有巧妙的配合關系。技能本身的獲得,是基于“時間的喪失”而取得的一種近期的直接回報,作為構成薇爾莉特自我存在的一種工具性基礎。而配合關系的存在,則是一種長期的間接回報。薇爾莉特時間的推進是看似理所應當的混沌,但實則是由這兩種技能的配合關系對于現實具體問題的除阻而實現的。
這樣一種配合關系的產生不是曖昧巧合的。代筆這一職業使得薇爾莉特的工作方式不是辦公室辦公,而是旅行式辦公,這就是薇爾莉特工作時開頭的自我介紹:“只要客人需要,無論天涯海角,都將使命必達,我是自動手記人偶——薇爾莉特·伊芙加登。”每一處辦公地點,都并非辦公式場所,而是生活式場所,充滿各種變化,為了適應這種輪換的陌生環境體系,作戰時所訓練出的觀察、戒備、格斗及運動等能力,就形成了重要的工作支撐。
因為具有這樣的配合關系,薇爾莉特每一次的代筆工作都能夠順利完成。這一“完成”,包含著“通行許可”的隱秘指令,換言之,薇爾莉特因為(能夠)完成A,所以能夠去完成B。工作是小同大異的(同:傳達自我對于對方的想法;異:傳達想法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這使得每一次工作的“完成”,都具有對于某種“完整”的“補完”的意味。這與拼圖相近而不等同,因為拼圖具有規定完整內容和為實現此而具有的拼接邏輯。然而薇爾莉特的工作具有高度靈活性,“規定”與“邏輯”并不占據核心。
實際上,薇爾莉特所被導向的“完整”并不現實存在。從表面上看,薇爾莉特所要“補完”的是對于“愛”的理解,這本身便不具有“完整”的裁定(具體論述參見前文:“時間:漫長”)。從深層次來看,每一次工作雖然是以“愛”為核心,但也包含著諸多其他方面的內容。這些共同構成的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本身指向的是無序與隨機。薇爾莉特所必須要完成的,是不能感知的“存在”——確實有“什么”需要“完成”,但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
薇爾莉特行進的過程只能是永恒進行的,以此而無限接近“完整”的觸感。而肉體的存在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實現概念化的飛升與抽象,才能使得這一行進過程不會中斷。這也正對應著薇爾莉特在生命的最后一階段——也就是肉體的結束之前——必須做出徹底的總結與選擇時,扎根小島,奉獻于郵政事業。
憑借之前兩個技能的配合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諸多成果,薇爾莉特得以在“此處”做出更多貢獻,從而使得自我成為受到敬仰的對象,并以跨時代的歷史見證者的身份,并在肉體衰亡后,形成“此處”的歷史紀念碑(例如“薇爾莉特紀念郵票”),以一種強烈的感染力和號召力,促使自我的事業能夠為后世所繼承與延續,于是那“未完成的完整”,由此便得以“永恒地進行”。
這就是“時間的報恩”,它的存在,正是為了使得薇爾莉特的“自我”能夠得以維持與行進。由于漫長性和欺騙性的存在,薇爾莉特實際承擔著強烈的精神重壓,盡管它們的本質目的是以曲折的方式服務于自我,但在目的實現——即最終薇爾莉特重獲真正自我、化為永恒的時間之前,對于薇爾莉特的傷害卻是客觀存在的,薇爾莉特對于傷害的承受由此也就成為了對于時間的恩賜。為了平衡傷害-造福的關系,則必須使得薇爾莉特這一主體能夠以“收獲”與“突破”的方式實現對于自我的認可,進而達到基本的維持,以全程永恒的行進來麻痹創傷的感知,以此得以實現意志支撐的持續,最終挺進到自我的終極升華。
時間的寵兒
薇爾莉特的迷人的氣質,正是來源于蘊藏在其內部的三個時間特質,即漫長、欺騙與報恩。“漫長”使薇爾莉特看起來頗為成熟與神秘;“欺騙”使薇爾莉特呈現出一層朦朧的脆弱,易引起來自他人的憐愛與關懷;“報恩”使薇爾莉特意志堅強,卓然不群。這三者本身是抽象的,但其因寄托于薇爾莉特這一實體上而得以被感知,薇爾莉特其自身也因此具有了多層次的形象特征。
然而薇爾莉特擁有這樣的時間特質并非玄妙之至,相反,這只是一個樸素的客觀現象,即“活著”的結果。因為“活著”,所以必然有從A到B的時間刻度,這就是“漫長”的基礎;因為“活著”,所以必然有面對和接受,這就是“欺騙”的基礎;因為“活著”,所以必然有行動的實踐,這就是“報恩”的基礎,換言之,其實大眾均有這三種特質。
所以,薇爾莉特作為時間的寵兒,其特殊性并不只是在于這三個特質的“擁有”,更在于“豐富”。行經的空間之廣,接觸的人事之多,承受的傷害之深——現實與精神“歷程”的多樣性與持久性,才使得時間特質在“基礎”之上能夠得以不斷豐富,才能夠使得這“活的魂魄”不斷成長,從而構造出一個具有鮮明獨立性氣質的“自我”,并在時間特質的助力下,實現對于“自我”的超越。
寫在最后
薇爾莉特雖已離去,卻以時間為新軀,將能夠永恒駐足于她受托代筆而游歷過的人們的腦海之中,成為記憶中難以被割舍的風景。這恰如詩人崔護再過南莊,春風桃花,人面不在,便在無可追回的悵惘中,輕易地捕捉到那時間的蹤影,只屬于“她”與“求訪者”的故事,由此而無聲地譜成了流淌千載的歌: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責任編輯:linlin]
標簽: 愛的權利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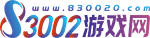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