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冬
早晨出門等電梯時收到老喬的微信,我媽走了。
我先回了信息,又給老喬撥了個電話說我現在回來,過了半晌老喬才說話,恩,你路上注意安全。
連著發了幾條信息推掉了這幾天的工作。直到電梯內的人問我到底進不進,我才回過神自己還站在電梯前,連忙擺手示意說抱歉。 回房間簡單收拾了衣物行李,從鄰城開車趕回西安。
我希望此時能盡快陪在老喬身邊。
岳母患病是在我和老喬結婚半年之后。胃癌,發現的時候是中期,第一次手術很成功,但不到一年迅速復發擴散,生命轉瞬進入以天為單位的倒計時。
雖然我的身份不該這么說,但岳母生前的確是個刻薄的人,對老喬尤甚,她此生所有的愛似乎都給了老喬的弟弟。
手術時是我與老喬鞍前馬后,術后也大多是老喬在悉心照料。
直到岳母離世,老喬弟弟來看她的次數屈指可數。
她卻對老喬說,你不要以為這樣我就會感激你,房子我已經過戶給了喬星,你別打主意了。后來又經常說自己復發是因為老喬沒照顧好。
我氣不過,我也知道還有更過分的話岳母不會當著我面說,但我沒見過老喬還嘴或辯解,并讓我也別。
雖然我與父母感情也算不得親密,但對此我無法理解。
岳母病情復發之后,醫生明說現在就是燒錢再吊半年命,你們家屬自己考慮。老喬依然固執的堅持治療,我們的存款迅速見底。
老喬說要賣房。我說你瘋了,說出口我就后悔了。
老喬說是。
這是她與她的戰爭,我無需理解,我只有奉陪。
守靈、出殯、追悼會、火化,入土安葬,一切順利。
雖然有殯葬公司全權負責,但親友迎來送往的招待也還得我和老喬張羅。
喬星全程哭的悲愴,是個讓每一位見者無不動容的孝子。
我絲毫不懷疑他此時對母親的真情,但當我聽見有人說怪不得喬媽更疼兒子,我心中滋味難言,郁結難散。
我很怕老喬聽到。
一周后的某個深夜,我感到身旁的老喬在顫抖抽泣。
老喬說我真的好恨她,可是我好難受。
我說,恩,我知道。
哭出來吧。
我抱著老喬,握住她的左手,輕輕按壓虎口處,我一時有些想不起是誰在什么時候在哪里告訴過我這樣可以緩解痛苦與難過。
2018? ?春
春寒料峭,新年后搬家的第二天,我穿著短袖短褲站在家門口瑟瑟發抖。
老喬今天有事回了她爸媽家,出門夜跑沒帶鑰匙的我就把自己關在了家門外。
手機電量見底,在我點擊發送“我跑步沒帶鑰匙,手機快沒電了”后的一瞬間,自動關機的黑屏讓我感覺自己被關在了世界之外。
新家是南二環邊上的二手簡裝小兩居,離我和老喬單位距離適中,兩站內有商圈、有地鐵,附近有大學校園可以散步,生活交通方便,小戶型將來轉手轉租也都容易,缺點是朝向臨街有些吵,價格略微超出了我們的預算。
不過雖然臨街,卻也因此才在容積率堪憂的均價樓盤中有了難得的開闊視野。
作為資深乙方,我深知價格、滿意度、時間三者不可兼得。房子是件大事,我和老喬預算有限,只能花費更多的時間。那三兩月我倆大半的業余時間都花在了看房與看房的路上,身心俱疲。
所以當老喬站在窗邊說“看,大雁塔”的時候,老喬久違的爽朗表情讓我決定就是它了。
裝修是件勞心勞力的事兒,大多是老喬在操心。
“不麻煩,硬裝不必動,軟裝有些小調整,也就挑家具費了點事兒。”喬遷新居的飯局上我喝了兩杯就不著四六的吹牛B,絲毫沒有注意到身旁老喬眼中的殺氣。
好在朋友們都十分有眼力見兒,連忙紛紛指著我鼻子說:“你個爛慫,不甘活兒還不知道把嘴嗶上。”
工作忙是借口,我承認我對婚姻仍然有一點可恥的逃避心里。當裝修成為婚前的最后一份合理緩沖期,我雖不至于刻意阻撓抗拒,但潛意識里不自覺地回避逃避。
我并非不愛老喬,只是對婚姻有所畏懼。
我和老喬在裝修與家具審美上大體一致,不一致處以她的偏好為準。
唯獨有一點沖突,老喬十分喜歡各種“智能”家居,而我對一切所謂標榜著“智能”二字的智障產品都有著深深的不信任與敵意。比如各種需要語音控制的設備,對著空氣說話實在是一件愚蠢透頂的事;各種需要app控制的電器,我認為實在多此一舉;又比如買家具時商家送的一個十分精致的“智能”垃圾桶,老喬非常喜歡。而我每次路過,它都會自動開蓋,仿佛是在耀武揚威地和我打招呼:瞅什么瞅,垃圾。我小肚雞腸,不堪受辱。
最終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唯有家里的大門沒有選用智能指紋密碼鎖。
然而此刻被鎖在門外瑟瑟發抖的我仿佛一個智障。
又一陣冷風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打了個冷顫,決定去樓下的便利店借充電器。
我自來熟,在便利店賒了一罐百事可樂和幾串關東煮,說手機開機了再付款。今天的步算是白跑了。
屏幕剛一點亮就彈出兩條微信提醒,都是老喬。
第一條,哈哈哈哈哈。
第二條,你先去樓下便利店呆著,有空調,我現在回來。
也許是便利店空調開的很足,這一刻我突然感覺沒那么冷了。
在我吃喝將盡的時候,老喬推開了便利店的門。
老喬問我結賬沒,我說當然結過了。又問我吃飽沒,我猶豫了一下說吃飽了。
老喬說,走,回家。
我莫名有種小學生放學偷吃路邊攤被卻沒帶夠錢,最后被家長抓包的羞愧感。
但又感覺身體在此時仿佛被這個城市中所有的溫柔所貼合包裹。
恩,回家。
第二天在老喬的“威逼”下我終于把家里大門換成了指紋密碼鎖。
2016? ?夏
天氣悶熱的讓人周末根本不想出門,午睡到傍晚的我和喬靜賴在床上陪她看《爸爸去哪兒》的重播 。
“你喜歡男孩兒還是女孩兒。”喬靜突然問。
我不認為我和喬靜的關系已經到了需要討論關于孩子問題的時候,這讓我感到非常惶恐。
但本能的意識到這是一道送命題,于是說都喜歡,想打哈哈糊弄過去,同時腦中高速回轉確認了一遍自己確實是一直非常注意安全的。
“你別緊張啊,我就隨口一問,你好好說。”喬靜追問。
我心說隨口一問?我信你個鬼。
“確實有區別,如果是女孩兒,以后就是我保護你們娘倆兒,如果是男孩兒,今后就是我們爺倆兒一起守護你。”我自然地說到。
喬靜半天沒說話。
我長舒一口氣,Bingo,正中紅心。
同時在內心泛起深深的自我厭惡,我竟然能言不由衷地將如此油膩做作的臺詞張口就來。
曾經有人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你知不知道你真的是一個爛人,你是我見過的最虛偽的人,你會本能地討好所有人,隨時準備著說對方最想要聽到的話,做對方喜歡的事,但實際上你是一個無比自私的人,你根本不愛任何人,你只是享受做一個“好人”的感覺,你讓我惡心。
我都承認,我全盤接受。
雖然在她說這些之前,我自認為說了這輩子最誠懇的話 。
有首歌怎么唱的來著,我說了所有的謊,你全都相信。
喬靜那天后來說了很多話,大多是她童年少年時一些家庭中不太開心的事情。
所以她特喜歡看《爸爸去哪兒》這類親子節目,且對家庭充滿渴望。大約是某種代償效應。
這更加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罪大惡極的人渣。
我很會討好人,但不怎么會安慰人。所以只好用秘密交換秘密,希望能用自己的不開心讓她開心開心。
我說你知道搖搖車么?就是給小朋友坐的那種“爸爸的爸爸叫爺爺”的搖搖車,我小時候特喜歡,小孩兒都喜歡。通常都是姥姥帶我去坐,終于有一天我爸媽難得的同時出現帶我出門玩,我盡自己所能的表演一個懂事聽話的”好孩子“,想讓他們倆都開心,即使是爸爸主動提出讓我去玩我最喜歡的搖搖車,我也只是小心翼翼地說我就坐一次,就一次,我保證不鬧著玩第二次。但他們還是吵架了。越吵越激烈,直到兩人扭頭分別離開,把我一個人留在了搖搖車上,他們都以為對方會回來接我,但都沒有,直到很晚姥姥才找到那家店帶我回家。從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歡坐搖搖車了。
喬靜聽完以后面無表情地說,走,吃飯去,我餓了,想吃火鍋。
一路上無論是路過小商店,超市,商場,但凡有搖搖車的地方喬靜都會前去問老板能不能讓1米8的我坐坐,商家當然是不會允許的。起初兩次我還勸她別逗樂兒了,后來看她興致不減也就由她去了。
吃完飯散步回家的路上喬靜依舊鍥而不舍,我說別鬧了。
喬靜說,你別怕,不管你想坐多少次想坐多久,我都會等你的。
Bingo,正中紅心。我不知道那一刻喬靜的心里會不會有這樣的聲音。
雖然那天最后我當然還是沒有坐搖搖車的。
雖然那天以后我依舊對婚姻充滿恐懼與抗拒。
但那天是我第一次覺得,如果是眼前這個人,也許是可以的事情。
2015? 秋
喬靜因為要做正畸,所以拔了智齒。
我因為拔了智齒,就順便做了正畸。
世事往往如此,明明最初的性格觀念和出發點完全不同的人,最后卻能恰巧共同抵達同樣的終點。
就像口味完全不同的我與喬靜莫名其妙成了飯友。
我嗜辣,喬靜喜歡酸甜口;我主食喜歡吃米,她愛好吃面;我喜歡可樂,喬靜喜歡百事。
呵,百事怎么配叫可樂呢。
恰逢當時我倆牙口都不太好,菜單的可選范圍進一步縮窄,正畸戴上牙套后門牙成了擺設,連肉夾饃都再無福消受。取最大公約數后,那段時間我倆最常吃的是某連鎖湯包店。
如今也常去。
在九月份我倆終于雙雙成功戴上牙套時,喬靜說這是非常值得慶祝的事情,拔掉智齒代表我們和腐壞的過去徹底再見,戴上牙套代表我們的新生活正在重新矯入正軌,于是約我去看陳奕迅的演唱會。
那一場的安可是《十年》和《夜空中最亮的星》。
十年之前,曾與我同行,消失在風里的身影。
我和喬靜牽著手,各懷心事。
演唱會結束后不好打車,我倆從省體育場沿著南二環壓馬路一直到大雁塔。
我想吻喬靜,喬靜說等一等,她要百度一下。
于是掏出手機三兩下操作看了看之后又把手機遞到一臉懵逼的我面前說,行了。
手機屏幕的搜索欄上寫著“戴牙套影不影響接吻”,百度結果是不影響。
事實證明百度確實不靠譜。
我倆的牙套卡在了一起,好痛。
喬靜說她今天不想回家了,我說好啊好啊。
喬靜說咱們去通宵唱K吧,我說那也行吧,就是我五音不全,唱歌不著調,特別難聽。
喬靜說沒事兒,我不嫌棄你,剛才演唱會的時候你跟唱不是挺起勁兒的么,也沒跑調兒。
然后又笑著說,我們又不趕時間,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
我點頭說的確,不過我心里的情話臺詞排名,《買兇拍人》中李棟全的“Camera ready”勝過《志明與春嬌》中張志明的“有些事情不用一個晚上都做完,我們又不趕時間。”
喬靜說那看來我們終于有一點是一樣的了。
第二天清晨吃肉丸胡辣湯的時候,喬靜說我收回昨天晚上的話,唱的不錯,下次別唱了。
我說你現在后悔已經晚了,說著又賤賤地唱了一句:
因為...
2014? 冬
...因為我喜歡,喜劇收尾。
結束了一段深陷泥沼的戀情,搞砸了一份曾經夢想的工作,我在這個冬天從北京滾回西安。
眾發小與狐朋狗友們得知我狼狽還鄉,紛紛前來陰陽怪氣地賀喜嘲諷,酒局隔三差五地排了一個多月,過了一小段日日聲色犬馬,夜夜笙歌的放縱日子。
報應來的比我想象中更快。
冬至那天起床后便感覺后槽牙隱隱作痛,老毛病,幾年前牙醫就勸我長痛不如短痛,把兩顆阻生智齒趁早拔掉,不然治標不治本,牙痛遲早反復發作。
晚上酒局回家后痛感愈發強烈,酒精沒有提供絲毫的麻痹作用,反而連帶起偏頭痛。一夜無眠,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痛的滿地打滾。據說即使是最重口的抖m也無法從牙痛獲得快感。
凌晨4點半我終于忍無可忍,囫圇洗漱后打車前往口腔醫院,心想一定得排到今日就診的第一號。
從車上下來我就看見一件“羽絨服”懸浮在醫院門口來回飄動,我心中暗叫不好,完了,我這是已經痛入中樞神經,大腦產生幻覺了。
最終還是疼痛戰勝了恐懼,踱步走向醫院大門。
走近我才看清“羽絨服”的真身,一個身材不算低的女孩,穿著一件約摸3XL大小的男式黑色長款羽絨服,衣服下擺接近腳踝,手臂完全沒入袖口,領口立起幾乎提到了下眼瞼處遮住了口鼻,劉海長發,遠遠看去可不就是一件衣服懸浮在空中的模樣。
后來偶然說起第一次相遇的情景,老喬說那是她從網上學的獨居女性生活小妙招:家里常備一兩件男款外套,在取快遞外賣時穿,能提升安全系數。
老喬在撒謊。
那天她穿的那件羽絨服上有著非常濃重的香煙味道,老喬從不抽煙,且對氣味十分敏感,每次我們吃完火鍋烤肉之類氣味比較大的東西后,老喬回家第一件事必是先把我倆吸了味道的衣服掛去陽臺,一套復雜操作處理掉衣服殘余的氣味。
所以那天要么是衣服的原主人剛剛離開沒多久,要么又或許是他已經離開了一些時日,而老喬刻意想讓他留在外套上的氣味散去的慢一點。
如果說我這個爛人還有什么微不足道的可取之處,那么就是我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必要的好奇心。
你不想說,我不會問。
每個人在心底都有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愿再提及的秘密。
而我們將要一同走向的地方叫做未來。
人生海海,你我皆若浮游,怎樣的幸運才讓兩只渺小的蟲豸在浮浮沉沉沉沉后相遇。
時間不留情面地在我們心中刻下一道道缺口,令我們窒息、墜落、靜止,直到彼此的缺口如齒輪般咬合,咔噠、咔噠,從此世界再度開始轉動。
春夏秋冬,又春夏秋冬。
兩個人又要一起經歷多久或精彩或無趣的平凡漫長時光,建立怎樣的羈絆,經過怎樣的成長,才能在心中真正把彼此當做家人,才能有自信成為對方無論何時都可以信任依賴的家人。
同甘,共苦,并肩,同行,一紙婚書,共同育養子女,以我有限人生經驗一時能想到的這些,似乎都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
此時此刻我依舊不敢說有答案,又或許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彼時彼刻我更是根本從來沒想過這些,痛覺也阻止了一切思考。
“你用拇指按住牙痛那側的虎口,持續保持節奏按壓,可以緩解一點痛感。”羽絨服突然開口說話。
我試著照做了一分鐘,不知是真的有效,還是安慰劑效應,似乎真的好受一點。
“好像真有點用,感覺好一點,謝謝啊”我說。
短暫的冷場。
“你大半夜擱這兒cos什么火影忍者呢,嚇唬誰啊?”我突然沒頭沒腦的來了一句。
“明明已經是早晨了。”羽絨服搞錯重點的答非所問,說話的時候看也沒看我。
我扭頭順著羽絨服的目光望去。
今年最長的一個夜晚已悄然離去,天邊隱隱泛起黎明的第一縷蒙白。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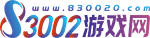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