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喪
注:文中的姥姥指的是爺爺的母親,小老姑的母親,鵬叔的奶奶
一
一顆摔炮落到凍硬的黃土地上,頃刻間劈啪炸了響。幾個玩鬧的孩子嘰嘰喳喳,其中一個穿藍色棉服的小男孩瞧見我們,喊著人來了,帶著他的三花狗立在路邊,一雙眼睛好奇地盯著人群。
我們這三十多個人在小老姑家吃完紅豆湯面條,烏烏泱泱往老屋走,走得很慢,隊伍零零散散。
小老姑扯著他的兒子,頂著風走在隊伍最前面。今天大喪,小老姑的大女子從定居的江蘇出發,中午就能趕到。
捏炮的小孩很快對路人沒了興趣,小手一丟,摔炮炸響在空空的牛欄上。
二
96歲的姥姥在老家的炕上閉了氣。年輕時逃難到西北的村子啃著紅薯葉葉香椿尖尖生了二兒六女,到現今兒孫滿堂,結出了累累碩果,平生最愛搓麻、人又和氣無聲的,一生無大病痛,因此算作喜喪。
一群白茫茫的人帶著新染成的紅孝布箍緊了孫兒輩的頭顱,憑紅白辨認著孝子賢孫。我耷拉著腦袋,看地上飛揚的塵,靜靜落在新搭的藍棚子上。
有個頭纏白布的“長輩”正攪合在一群紅孩兒中玩鬧,嘰嘰喳喳,與上房里不時傳出的慟哭聲形成了鮮明對比,匆匆忙忙、亦或無所事事的親戚們路過,都要刻意朝著那抹白或嚴肅或嬉笑地發難:“鵬,奶奶走了你咋不難過?”
李鵬是我小老姑的小兒子,因為生病高燒不退成了憨兒,三十多歲的年紀卻時常瞇著眼,以一種天然的憨態參與到孩童的玩樂中。
從這憨病落定以來,小老姑的紛憂鼓滿衣襟,背也彎了,聲更啞了。
他不高,很壯實,平臉上安了個斜眼睛,說話黏黏糊糊的,干活卻干脆利落,只是愛吃,各式的點心各樣的菜式各類的零食沒有他不愛的。因為貪嘴這一點,再加上智力缺陷,我們一家子人回老家總是會惦記著這個可憐人,帶些村里不常見的吃食。
我叫他“鵬叔”(發sou音),其他人叫他“鵬兒”亦或是全名全姓地喊“李鵬”,總之,旁人總是以可憐他的姿態來同他說話,拿他取樂,因為親戚的緣故不至于太過分,我不喜歡看鵬叔被逗弄回答不上的窘態,把視線移到大門新貼的白挽聯上。
老家已經許久未有人住,到處都是煙、塵、土的火氣。姥姥病重的時候我跟隨母親看望過,那時她已無力睜著眼,得靠人用手指推些草莓醬泥來進食,躺在縣城的床上,氣若游絲,直到大限臨近,強撐著精神回了老家,才真的沒了鼻息,溘然長逝。
姥姥在時很少和我說話,老人家久居西安,那點親情就像迎風直上的風箏,因距離被撩撥得斷了線、沒了跡。
三
這個位于西北的村落慌慌落落迎接著四方來客:一層是鄰人鄉黨,需登門拜訪、送紙奠事;另一層是親朋好友,要禮數周全、與人同悲;最讓孩子們喜歡的是專事紅白的職業人,面包車里拖下來大大小小的各式道具,活潑的是樂人,紅潤的是掌勺廚師,我最貪那碗辣子烹豆腐;最后則是尋著味也來撿拾骨頭的狗子,豎著尾巴沖著人群叫嚷。
我今夜已記不清恐嚇了幾條狗。棚下坐了三桌,正等著上菜,鵬叔久等不到,耐不住性子要往屋里找廚師,正巧見到我在打狗。
他掏出兩顆糖來,徐福記的花生酥,“晶——晶”,鵬叔笑呵呵的。
那只黑皮狗趁機撿了塊排骨就跑。
北方冬天的夜晚來得很快,從外看,當作靈堂的上房顯出幽閉的氣氛:冷風吹不動厚厚的帳幔,長明燈亮著軟而黃的光,臥在籠子里的“守喪雞”不安躁動著,咯咯聲冒了半個音就隱沒在黑夜中。
我被母親叫進了上房。老家的宅子窄小、偏狹,長條屋子排列成三組,中間橫著一棵老姑幫忙新種的櫻桃樹,一路上都是裝滿著肉菜調料的盆盆罐罐,不知顏色的狗在門外低低地吠叫。
黑白兩色的靈堂在夜里更恐怖了,想著前不久瞟了幾眼的恐怖片,雖有些抗拒,也只能硬著頭皮把一身冷氣關到了門外。
“呀,晶晶來了呀”,有人招呼著我坐下。
屋子里坐滿了各個年齡的女人,鋪滿了五色韶光的被子,空氣里聞得到木柴火燒的繚繞香氣。
今晚要給躺在冰棺里的姥姥守夜,一伙女人拉家常有,摸牌玩樂有。姨姨拉著母親,問我幾歲了,應該是快要畢業了,找好工作了么......正巧旁邊的麻將桌里有人連開兩杠,一陣熱鬧,那姨姨才不再問,去看牌局。
四
姥姥的黑白相片沉浸在燈光里,目光顯得更柔和、人更寬容和善。
我的背挺得更直了,而像我一樣拘謹的人面前正坐了一個。那是個印象不深的黑臉蛋女人,嘴皮干燎起了皮,正貼著爐子取暖。
見我仔細看她,那女人局促一笑,艱難地從粗糙的孝服口袋里掏出小圓橘子,擺手示意我:“吃——吃!”
我的手里被塞著個橘子,小小的,涼涼的。
這種熱情實在讓人不好意思,我摸了摸,從兜里拿出一盒旺仔牛奶,報之以李。她那黑眼睛更亮了,連忙推開嘟囔著:“不要!不要!”她拒絕時發出的嗯嗯聲就像哨子,尖銳而有力,我一時怔愣,猛然想起母親曾經說過鵬叔新娶了媳婦——那媳婦腦子也是不行的。
在一旁與母親正說話的小老姑紅著眼,淚痕猶在,轉過身叫她拿了就是。
這個女人就是鵬叔今年剛過門的妻子——潔娃。
小老姑煩惱鵬叔的前半生,操心他的后半生。老姑父是不如她這般操心孩子的,而小老姑是個堅強的女人,就像決定在洼地上種二畝櫻桃一樣不容他人置喙,這個傳統的老人力排眾議堅持讓我的叔叔李鵬一定得成家——等樹上掛滿紅果,等溪水淌滿洼地,等他的兒子成家立戶,她才能撒手得干脆。
聽母親說,小老姑為了鵬叔的婚姻“上當”多次:二婚女人卷走見面錢、癱瘓丫頭要人照顧的......總之,全須全尾、后天智殘的鵬叔一面應著各種相親局,全不明白母親對著豬蹄髈為什么會流下細碎淚水。
潔娃,就是在小老姑心灰之時入的門,據說是腦膜炎發作后腦子就成了那樣,以四萬的彩禮錢被父母抵掉、走到那個鋪滿流光的院子。
平心而論,小老姑的家底在村中是不薄的,又靠著幾十年的果錢把院子收拾得整整齊齊,堆砌得亮亮堂堂,只是因孩子是個癡兒,在村人眼里不免可憐見的。
如果說鵬叔的價值發揮在那十幾畝果園上,那潔娃的價值就如同洗衣機里的泡泡,輕輕一戳就沒了影。小老姑是開心了一陣子的,她心里住進了艷陽天:這個家庭總算是像樣了,但她隨即發現,這個新兒媳憊懶,用不得使不得。
“叫她洗衣服,好不容易教會了用洗衣機,人一走她就嫌洗衣機慢,一個勁地轉。”
“叫她剝花生,一個下午就剝了一顆!”
這些話當然不能讓潔娃聽見,到底是個病人,聽了會難過。我們都明白,潔娃遲早要回去自己家里,小老姑他們是不愿意再擔一個包袱的,這一家子,維持著微妙的平衡。
五
而我小老姑的眼淚又是為誰而流呢?她三十多年的痛苦遭難在她三姐身上重現了。
三老姑的孫女發育遲緩,是常人說的智力低下,醫學沒有法子避免所有不幸。總之,兒媳生了二胎弟弟后便對這個女兒棄之不顧,自己的兒子也是個懦弱的,去了城里打工,像丟包袱一樣把一個嬰孩留給了這個靠做白活為生的老人。
三老姑從來沒告訴周圍親戚這樁不幸的事,在那個秋風也刮不進的閉塞小院,在那個疊滿元寶銀幣的泥土小屋,她把那孩子像敬獻貢品一般安放在平幾上。嬰兒因為饑餓會啼哭,她便在門外熬了一天,整整一天。
很早就聽不到細碎、孱弱的哭聲了,三老姑推開門,摸進被里,那小孩子仍有氣息。
現在孩子七歲了,很安靜地吃著零嘴。
旁人聽了幾遍這樣的苦事也只能勸慰著三老姑她們向前看,日子會好的。我的小老姑每聽一遍就要抹眼淚,她當然明白這種行為是什么。聲音低低的,她說:“我是不會叫他們生了,等我快走了,我就把他(鵬叔)一起帶走,不拖累大女子。”
當夜我睡得并不踏實,母親仍在守夜,我只覺得外面吵鬧的狗十分該死。
這世界竟人少狗多嗎?鄉下的狗是會抓蝎子的,現在蝎子少了,是季節的緣故么?捉蝎子的人也少了,村里簡直看不到過去的人了!老家是要拆了的,房子也沒了!不過,爺爺說是要蓋個更大更好的屋子,我想著那未來更大更好的屋子,視線飄得越遠,終于睡著了。
六
等到了白天又是一陣忙碌,每個大人轉得像陀螺,忙不不停歇。廚師開了火,土泥爐子扣著大鍋,鍋里紅油豆腐翻滾著,無事的小孩守在爐前,看著廚師拋粉絲,撒蔥花。紅案上端著四碗辣子烹豆腐,送到屋外藍棚下,要出力氣的又要五個白饃,要為后面繁多的儀式做好體力準備,而棚后坐了一桌熱鬧的,一幫人擦著樂器,那吹嗩吶的逗弄小孩,樂音像黃雀跳枝忽上忽下。
這熱鬧處竟沒有鵬叔在么,稀奇了,他是個見了人堆就要湊的“孩子”,我兜里揣著幾塊酒心巧克力,正想拿給他。
幾個年紀大的老人由家里人搬來幾凳,等著送靈的白戲開鑼:那演出的女演員正開嗓呢。穿著便服的女演員見人多了,起好調子,一出口就是有名的“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嘆,
思想起我兒夫好不慘然”,引得眾看客興奮起來,好不熱鬧,那失去故人的哀傷就這么淡了淡了。
姥姥要正式下葬了。
裝著姥姥的棺木被抬進靈車里,那個松木制成的龐然大物甫一登場就讓空氣瞬間安靜了,隨之而來的悲傷和哭聲混合著哀樂,響徹云霄。
車前的臺案擺著各色祭品,最乍眼的是那頭插蔥的豬頭。
孝子賢孫們向著靈柩下跪,一跪再跪,村人在看著我們,大人抱著小孩,小孩聽著吵鬧。
鼓樂細吹細打,姥姥生前喜歡聽秦腔,正演到《孟姜女哭長城》這一折戲,那調子起得悲愁,皮鼓錘得哄響。好一會子,那女伶已起了唱詞,那昂揚的鼓聲還未歇止,反而亂了節奏,顯出極大的不和諧。
鼓手的小槌已拿捏停放在鼓面上,咚咚聲更急。靠近老屋的人有幾個尋著聲走,我也跟著。音響放出的哀樂蓋過了所有聲音,那時有時無的敲打聲像要炸裂一般,引著我們到了上房門前。
上房門被鎖了,妍綠經風吹雨淋成了舊色,玻璃窗前貼著一抹白影。
咚咚咚。
堅實的門顫動著,門前的鎖也跳躍著。
透過窗看,鵬叔那憨態的臉在玻璃窗前變了形,他眼淚橫流,把心焦熬成嗚咽聲,大手錘著木門,只顯出半個身子。
我攥緊了兜里的巧克力,不知道該怎么安慰這個可憐人。
是小老姑擔心鵬叔受不住儀式上的跪拜,又擔心他的癡傻,于是將鵬叔關進了上房。
他睜著那雙淚眼,嗯嗯著,只一個勁地喊“奶奶”,求我們開門。
圍觀的大家都淺淺地憤怒了,有幾人端來熱水和毛巾,給鵬叔擦著臉上的淚水、鼻涕。
癡人才有真心啊,在場的各位心里不免有些感嘆。小老姑站在墻角,像被犯了錯的孩子一樣,拘謹地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
那一張熟悉的、癡傻的臉重又見了天日。
門開了,我們雪白的隊伍要送姥姥安睡了。
七
白泱泱的人群排成幾列,往村邊的西山走去,那里是姥姥將要沉睡的地方。
天上炸響著禮炮,山路并不好走,得時刻盯防著松軟黃土,一切都黃澄澄的,顯露出紅日余暉。姥姥的墓前移栽了棵青柏,柏前是萬古長青。
白幡、花圈、紙馬、紙牛、仙童、玉女、仙鶴......姥姥和我們隔著一個世界了。
大火愈燃愈烈,煙屑把我們熏成了黑白世界,隔著塵霧,墳前的各色動物人物有了生命一般,隨著火光扭曲伸轉。
“鳥!”
“馬!”
“牛!”
一眾人哭喊著,念著那個過世的人,而鵬叔卻指著紙扎叫嚷著,他甩著撿拾的木枝條,跨著干涸的水渠,臉上洋溢著歡樂的笑容,看著男男女女哭泣。
火光在空里浮現,金色的、紅色的、灰色的,那是被風卷起的冥幣紙鈔。
......
回去的路上,一輛蹦蹦車拉著幾位出行不便的老人下山,車后尾斜坐著年輕力壯的鵬叔,一條腿蕩在黃土上。
車開得愈遠,就像火愈燃愈烈——鵬叔的行為讓很多人不快了,不止一個人出了聲,男男女女疊加到一起,人們大聲、嚴厲地向著那個憨兒喊:
“鵬,下來!”
“你坐什么車?”
沉浸在痛苦中的小老姑用了勁,喊破了聲,她吼:“他做過腳的手術啊,他疼啊!”
遠處的村子寂靜平和,玩耍的孩子又三三兩兩,樂在一處。
青天白日里沒了聲音,作喪的禮炮響了又響,整整九十六聲。我按了按耳朵,轟轟隆隆,四周沉寂包容,只天上留下了淡淡煙氣。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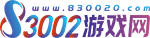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