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教父》是我百看不厭的一部作品。
尤其在四五年前,我正處于考研失利,工作又沒著落的階段,幾乎是看一次哭一次。那時候身為“社會邊緣人”——家里蹲,對電影中的homeless們很是惺惺相惜,時常從他們的言行中發現“自己”,并因為看到他們榮獲救贖而對自己的未來也鼓起了微茫的勇氣。
現在想來,日本的homeless和中國的家里蹲,何等奇妙的匹配。而我居然能從他們身上獲得精神力量。這種特殊的共情或許說明:同是天涯淪落的人們總能像病友一樣互相理解,盡管他們之間有幾多國別與文化上的差異吧。
——那既然說到病,我們之間共患的是什么病?
簡而答之,是心病。
一個人,一個好端端的人,為什么會走向離群索居、徹底躺平的狀態?從我自身而言,主要是因為自己沒法再去相信了:一是羞于相信自己了,二則是不愿再相信別人了。
因為羞于相信自己,所以覺得自己“做不好事情”“活著沒有意義”,于是躲進家中那方小小天地里;過了一段時間,又覺得長此以往對不起家人,怕“自己成為負擔”而“耽誤他們的生活”,于是選擇離開。
走上街頭之后,看到一張張小日子過得還不錯的臉龐,一副副欲望強烈、野心勃勃的表情,又覺得自己不配做他們的同類,生怕遭到白眼和傷害,終于怯怯地躲在一邊,忘掉來路隨波逐流,得過且過地揮霍掉“上天分配的”剩余時間。
如您所見,這種病初期總是以自我懷疑出現,而后往往要不斷擴大,不斷變重。對自我和他人產生懷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天長日久不能得到矯正,長期不能樹立信心。人若失去信心,只會心陷泥潭,越陷越深。
而事實上,很多homeless都不是先天就想去流浪的。看一些人的生平,可以發現他們幾乎都是先出現心理問題,而后因為郁結的問題太多,自己從心里面否定了自己,繼而才否定了構成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放逐掉自己的。
因此不是外界因素,是內在的懷疑導致了他們的出走。放到電影里,這樣的人是homeless;放到生活中,我相信擁有這種病的人并不在少數。現代社會中,巨大的生活壓力和不斷被強迫的自我,可能使我們中的很多人患上這種隱疾,活在“不敢相信”的狀態。今敏先生一定發現了這點,這才有《東京教父》里三位主角的出現。
當然,我覺得這里形容主角身份的homeless可以看成一種隱喻。Homeless,沒有家的人。它不光指身體上拋棄了家庭,更指精神上無所皈依。《東京教父》最后三個人都獲得救贖,也不單指他們回到了家庭,而是指他們的心重新住進了“home”。
心有所依了,心被保護起了,心病自然就好了。因此治療他們,就要從讓他們相信開始。而世間的苦,說來說去也大都是由“不相信”引起的。
有趣的是,完成這個救人補心任務的,既不是三位主角的家人,也不是所謂的神明,而是一個跟他們毫無關系,剛剛出世的嬰兒。
嬰兒,作為上天派來拯救我們的人,有時候她象征著神明,有時候她象征著家庭。我雖明白這點,但一開始并不理解讓嬰兒“清子”擔任救贖者的巧妙,直到后來我自己思考了這部電影的劇本。
如果讓我編劇的話,為了挽救三個homeless的靈魂,我可能會拿出最直接的方案來:
三個人既然拋棄家庭,那就讓制造機緣巧合讓他們回去吧;精神上無所皈依,那就讓他們信神吧。然后編一個緊張的情節,讓三個人更加團結友愛,故事在這時結束,收獲觀眾含笑的掌聲。
但是顯然,編劇者早就想到了這些。這部電影中不乏我們常人能想到的情節:比如家人在不斷找他們啦,不斷有機緣巧合讓他們和家人會面啦;而且這三人也都樂意相信神明,他們會去教堂領施舍,會在絕境中互相關懷,會時不時流露出團結友愛……
但是,真要這樣編劇了,這個故事還有說服力嗎?一個人的心病,如果全靠別人之手來治愈,還會激發出鼓舞他人的力量嗎?
顯然是不能的。一個人的心病總要靠自己來醫治。
像老Gin、花兒和美由紀這樣的奇妙組合,雖然很像一個神明撮合出的家庭,雖然彼此間也有凡人的友愛和溫情,但這個家庭始終是病態的。
他們三位代表著整個社會被自我放逐的“父親”“母親”和“孩子”,并不能靠家庭的力量將自己救贖出來,而是如同三位病入膏肓的病友,一直在原地打轉。
心病難醫,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東西,是無法激發出他們的自救意識的。同時這個救贖人心的東西,也必須是能打動觀眾,激發觀眾的惻隱與認同的。因而這個角色,理當由一個純潔的嬰兒承擔。
而事實上,嬰兒之于人類,本身就是奇跡般的東西。面對著那種天真無邪,代表著神明饋贈的眼睛,沒有人會不心生憐愛,沒有人會不感動于生命。進一步地,沒有人會看不到、會不聯想到最初的自己。
啊,對,那個最初的自己。以及由此而想到的那些最想做的事,那些最信賴的人。
這些東西本是構成我們自己的最初的基石,是我們行走于世的最本源的東西,是不勞他人澆灌自己就可以成長的種子。它們就像永不背叛我們的寶物,一直深藏在我們心底的保險箱里,只不過后來被我們忘記了,偶然間蒙塵了而已。
因而一旦被人提點而出,它們就會像一面鏡子一樣立在我們面前。審視它們,我們重新發現自己,重新找到依傍。因此,它們就是拯救我們的最決定性的力量。
故而,在最危急的時候,懷抱嬰兒準備跳樓的幸子才會在嬰兒的臉上發現幻覺式的那句“我想回家”。這不是嬰兒在告訴幸子,是幸子在告訴幸子。是幸子的心里生長著對“家庭”的渴望,它才會在那個時刻跳出來拯救幸子。
正因為如此,老Gin、花兒和美由紀才會在撿到嬰兒后變得想要回家。他們三人并非都斬斷了回家的念頭,而是一直壓抑著這種強烈的愿望,用自我麻醉的手段來騙自己的。這些愿望如同被堵塞的洪流,只要一個重大的契機,就可以自己沖破堤壩,蔓延心頭。像老Gin拿出為女兒婚禮存下的皺巴巴的三萬日元,像美由紀朝家里打去那一通電話,為什么要這時候才去做呢?那是因為他們奔波在幫嬰兒找媽媽的路上。因為渴望幫“嬰兒”找到家,于是勾起了自己對“家”的念想。
這不是外界在強行幫助他們,是他們自身在幫助自身。心里面既然燃起了重回家庭的渴望,自然就有了一份對自己和家人的信任,于是終于發現了歸宿,人就由內而外地回歸了。
為什么會回歸呢?因為心里一直裝著家呀。
但為什么等了那么久還不回來呢?因為之前一直不肯相信呀。
只有相信了自己可以擁有家,才能重拾信心,回歸社會。
當然了,說到底,電影也只是電影而已。
《東京教父》雖然把故事講得如此圓滿,但里面出現了太多巧合和奇遇,時常讓人感受到一種不真實性。(就像最后時刻哈娜醬(小花)靠著上升氣流,懷抱嬰兒逃過一命,怎么看都像是一樁強行為之的“奇跡”。)
而來看電影多有成年人。成年人與少年人的一大不同,就是他們不輕易相信“幸運”。
關于這一點,導演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但是通過一些細節,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某些立場。
比如說,哈娜(花兒)手捧嬰兒走在路上,連續發生了幾次車禍,雖然是幽默的場面,但是每一個車禍背后都讓人細思極恐。
又比如那位人生最后的理想是死在榻榻米上的大爺,作為一個真正的homeless,他的慘狀不就是老Gin不回家的必然結局嗎?
還有,假如說老Gin沒有遇到自己的女兒,沒有中那個全是1的大獎;美由紀沒有打通父親的電話,而父母又離異了重組了家庭的話,那么故事還能圓滿嗎?
真實的生活往往是不美好的。我想導演在構思的時候,一定充分認識到了這個故事的荒誕性。也許他可以明白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但是他沒有那么做。他把真實隱藏起來,只是在不經意間才流露出他對這個世界的“惡趣味”。
就像在老Gin遭受小混混毒打的時候,他故意把遠處樓上的燈光做得像格斗游戲里的血條一樣;
就像哈娜在追憶健君的死亡時,說他是“踩中了浴室的肥皂”而死。
導演刻意的夸張,顯然是想告訴觀眾:我們是在故事里,我們只是在表演奇跡。而他自身可能與“奇跡”還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甚至在這段距離里,他還在冷冷地笑。生活的真實并沒有缺席,它們只是被隱藏起來,不占太主要的位置而已。
但即便這么說,這也不能說明創作者心中沒有對世間的溫情。換言之,如果明明知道世界的不圓滿,還要為大家講述一個圓滿的故事,這種行為本身就意味著高尚。
《東京教父》并不是講述“奇跡”的故事,它只不過是借用了“奇跡”的方式來勸誡人心罷了。
而在生活中,奇跡之所以叫奇跡,是因為它還是有可能發生的。——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我們一般把它叫做“不可能事件”——因此,縱然生活中到處都是遺憾和壞運氣,我們也得承認奇跡的存在。
這里的承認并不是迷信,只意味著“相信”。這部電影仿佛在充當大家的“妄想代理人”,它通篇要告訴人們的是:“別放棄,奇跡也許會有呢?”
看著動畫里三個一無所有的人,為了嬰兒而奔波在冷漠的城市里;看著這世界里被貶損被傷害的人,因為一絲善念相互幫助的時候,你不覺得這些行為就很配得上“奇跡”的降臨么?
反正大家上影院都不是來領受絕望教育的。那不妨趁這個機會,把大家對人世間的暖意都釋放出來。
當我們丟掉對家人的苛責和懷疑,反思他們留在心中的溫暖和好意,難道不會在胡亂填詞、瘋狂走調的《歡樂頌》中重拾自己對生活的信心?當我們看到他人的浪子回頭,于是也表達一下對家人的寬恕,不也是人生一世應該有的態度么?人們在貧窮、困頓的牢籠之下,依舊向他人伸出援手,不正是人間最平凡也最讓人感動的真情么?
何況嬰兒天真的微笑,在片尾也向每個人眼中閃耀了。我相信任何人的心中都會被那如同溫暖陽光的微笑照耀到。
而能讓人們沐浴到這樣好的陽光,不正是很多文藝工作者畢生的追求么?
固然,生活是苦的,活著也讓人不夠愉快。但這不代表著我們不該努力,不去送一段朝暉給別人。
“即便我們已經洞悉了世間所有的真相,也不妨礙我們在泥濘和腐朽里,為你開出一朵花。”
這或許是一句美好的想象,但也是人類自身神性的體現。
套用一句幾乎被用爛了的名言:
人類獲得幸福的途徑只有兩條:那就是等待和希望。
相信希望,本身就是一種救贖。哪怕是騙騙自己,逼著自己相信什么,也比什么都不做強呀。
我們這種愚凡的人類,不正是靠著相信的東西才得以生活下去嗎?如果我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獲得愛和關心,那么漫漫人生路中的凄風冷雨該怎么度過呢?讀到這里的朋友,您以為呢?
最后要說的是,身為家里蹲的我,最后考研還是考上了。初試的時候,我考了我們這個專業的最后一名,處于復試岌岌可危的地位。復試的時候,我是硬著頭皮去的。然后復試仍舊是最后一名,只不過,這次是錄取的最后一名了。
人們或許覺得這是巧合,但我覺得這是奇跡。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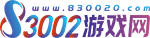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