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4月數據,希臘新冠確診病例超過321萬。一個媒體人出身的中國留學生,便是這321萬分之一。他去年10月到希臘,3月查出陽性,然后開始獨自應對,直至轉陰。他專門撰寫6000字抗疫日記:他是怎么感染,怎么居家用藥,怎么熬過一個人的胡思亂想……
1
我陽性了。也許更早幾天,我就已經被感染了。但我不清楚,直到3月8日早上自測結果出來。
那天早上八點,我剛從臥床26個小時中醒來,感覺很差。我頭疼、咳得厲害,而且渾身酸疼,一點都不想動。上午九點鐘有課,我在考慮要如何請病假。
上海的一位朋友發來消息,希望我幫她下載一份文檔。我勉強起床,打開電腦。在下載文檔的間隙,我洗了把臉,穿上了厚厚的羽絨服,出門到樓下藥房買自測包。雅典的這個3月上旬格外冷,天氣預報說過兩天還要下雪。
藥房里只有我一個顧客。柜臺上樹立了玻璃板,專門用來隔離顧客和藥劑師。藥劑師對這么早就有人來幫襯他的生意感到很高興。我開門見山,說要一個新冠自測包,他面無表情:“三塊五”。
說明書是希臘文,好在我之前努力學過,看懂了在什么情況下是陽性、什么情況下是陰性。我撕開塑料包裝,把取樣棉簽拿在手上。
根據說明,棉簽捅進鼻孔應該達到2.5厘米,然后攪動五圈。我手掐著大概2.5厘米處,充滿了捅鼻孔的恐懼。在5分鐘的心理建設后,我把棉簽伸進右邊的鼻孔。剛攪動兩下,我就趕緊拔出來,打了個噴嚏;換個鼻孔繼續,還是兩下。我把取樣戳入試劑,按照規定攪動六圈,之后扔掉棉簽,將試劑用另一個蓋子封上,倒立,將試劑滴入檢測儀。我擠了四滴。
根本就不需要等待15分鐘。20秒不到,試劑滲過試紙,在T處留下一道紅色印記,接著繼續往C的方向滲透。我看到T處的印記,就知道結果了。不到一分鐘,試紙印記穩定下來,清晰可辨,兩道紅線:“θετικ??”(陽性)。我拿起字典,又查了一遍這個單詞的意思,還是陽性。
這個時候是早上8點43分。我不用去上課了,要趕緊給老師寫信請假。昨晚的考古學論文,可把我難倒了。我頭昏腦漲,抱病閱讀滿是看不懂的術語的論文,勉勉強強,終于趕在最后期限敷衍地提了一個問題,以證明我的確是看了材料。
老師很積極地反饋說,“沒明白你的意思,建議你明天課上當堂提出。”我嚇得不敢回復。現在,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等我再回去的時候,他肯定已經忘記了這事。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之前是他一直催促我做檢測。他告訴我應該馬上打電話給醫生,按照當地的指引操作云云。可我只想去睡個回籠覺。過去兩天,我一直被我理解的“重感冒”折騰,我都忘記自己是不是發燒過,也不記得去買個溫度計。
下午醒來的時候,我收到北京朋友的短信,問我“醫生咋說”。我感到很愧疚,感覺辜負了對方的關心。我馬上查詢了我之前接種疫苗的那家醫院電話,打了過去。
電話里是希臘語,大概是什么情況下按1,什么情況下按2。我聽懂了數字,但聽不到前面說的啥。我依據經驗,按了0。電話收線了。
我感覺到很挫敗,換了一家醫院打。這次有人接聽了。我告訴他:“我感染了,陽性,請問我應該怎么辦?”對方問了我的年齡后,就丟給我一句話:“請注意休息。如果你感覺很嚴重,請來醫院。祝你早日康復。”
他還少說了一句“多喝熱水”。因為我剛學的希臘語課本中“看病場景”的對話里,醫生告訴病人說:“我給你開點退燒藥,你要多休息,多喝熱水。”
我又把這篇課文復習了一遍,想起我的希臘語老師近期也感染過。我跟她請假。她發來不咸不淡的幾個字:“你陽性了。”過了一會,她又發來一行字:“記得吃Depon,早日康復。”
Depon是一種本地的泡騰片,我之前有時在課堂上感覺頭疼犯困,她就推薦了這個藥給我,2.8歐元一盒,8片。我找出來,沖了一片喝下去。這個時候我想起來我已經差不多40個小時沒吃飯了。我兩腿發軟,感覺走路在飄。我給自己煮了兩碗粥,煮了兩個雞蛋,拌了白糖吃了下去。味覺還在。
我又翻回去睡覺,直到下午被電話吵醒。
2
出國之前,我對感染這件事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尤其是希臘這么一個人口只有1200萬的國家,這幾個月每日新增都穩定在2萬人左右,高峰時期日增5萬人。
所以,盡管不愿意,但我明白自己大概率是要被感染的。
我在這里的生活跟我的希臘語詞匯一樣單調,每天兩點一線,基本不去市中心。按當地政府規定,在接種疫苗之前,我每周都要做核酸檢測。我在國內沒有打疫苗,來這里之后,先申請了當地的社保號,之后才能預約打疫苗。社保號申請只要10分鐘,但取得接種資格花費了2個月。
確診感染后,我也曾努力回想過,究竟是在哪一刻被感染的。病癥初起是在3月5日星期六的夜里,那天白天我去市區買了兩本書,回程經過一家彩票店時買了張彩票,然后去埃及朋友的家里吃晚飯。回來后,我感覺到嗓子略有不適,懷疑是剛才的北非咖喱和埃及紅茶導致的。
第二天是周日,我外出散步,路過一處古羅馬時代的浴池遺址,遇到了一只烏龜和一只貓,我還給它們拍了照。初春的太陽很暖和,我坐在車站的椅子上瞇了十幾分鐘,之后起身回家,到家后覺得發冷,也許是在長椅上打盹的時候著涼了。我吃了一粒感冒藥,倒頭就睡。這一覺,睡到第二天早上,我發覺已經下不了床。
我得了“重感冒”。干咳、鼻涕、頭疼,渾身酸疼無力。我裹緊被子,又繼續睡,直到傍晚才有點力氣說話。我一整天都沒吃飯。從之后的情形來看,這天是我最艱難的一天。
我告訴北京的一個朋友,我可能確診了。他強烈建議我去檢測一下。我無力起身,于是就把這事拖到了第二天3月8日。
3
一個電話吵醒了我,是老師打來的。除了慰問之外,她建議我去做一個詳細的PCR檢測,“因為自測可能不準”。我知道她在安慰我。自測結果的正確率是98%,只在理論上存在誤測的可能而已。
“不要騙自己了”,我對自己說。當然,在程序上,我需要把自己感染這事納入政府的數據系統中,不管是未來病情惡化需要住院,或者康復后領取證明,都需要一個正式檢測報告。我打電話預約了一個PCR,約了第二天中午12點之前去做。
我看了一下表,大概是下午5點半,北京時間臨近午夜。我又望了一眼扔在桌子上的檢測試紙,兩道杠有點刺眼。自測試劑的包裝盒還在,我拿起盒子仔細看了看。這個自測試劑是杭州生產的。
第二天,3月9日,我幾乎掐著點,在12點前到了檢測機構。我支付了47歐元檢測費——確診期間我最大的一筆花費。醫生在咽喉、兩個鼻孔等3處取樣。回去的路上,我拐進藥房,買了一支溫度計。
購買溫度計,是我對這件事開始認真對待的第一步。我不清楚在我臥床期間是否發燒,也不了解身體狀況,這是非常錯誤的措施,我得糾正它。我在當天下午第一次量了體溫,36度。幾個小時后,也就是下午4點51分,我收到了郵件提醒,發件人顯示,這是我的正式檢測報告。當時我正在學的幾個希臘語單詞是:頭暈,咳嗽,發燒,感冒,牙科,神經科等一堆醫學類名詞。
報告中的“POSITIVE”(陽性)是紅色加粗標注的,后面還附帶了CT值。希臘衛生部的消息說,今日新增感染23335人。這份檢測報告,將我置于這份數據之中。通報還說,當日新增死亡61人。
斯多葛主義者慣于凡事多往壞處想,降低預期,這樣一來,當壞事真正降臨時,一切都在預料中,就不會感到失去什么。
所以我就想,我在去年10月就應該感染,而我竟然幸運到5個月之后、而且在打完疫苗之后才中招,何況這些數字跟平時一樣,并無出奇。而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巴黎隊在一場贏球概率在6成以上的比賽中輸給了尼斯隊,我連這張彩票都沒買對,怎么會買對千分之幾的死亡率呢?
我精神恢復一些了,感到需要找人聊聊天。我出來讀書以后,數次被人問起“你在外面有沒有想家,想念國內的朋友”。這個時候,應該想念他們了。我在老同事群里問,“你們最近有啥新變化嗎,說出來聽聽?比如誰分手、誰失業。”
其中一個前同事群里,S說她的車被刮了,車后攝像頭被人偷了,她準備調監控把那人揪出來;W剛離職了,下一份工作準備去北京;X在隔離期間牙疼,臉也腫了,還發了一張自拍以茲證明;Y說她密接了,正在隔離;L說他最近發掘到一套不錯的古籍影印本,可以云盤發給我。
北京的一個群里,H說自己的基金;Y說在單位睡了兩天,就像在網吧包宿;J在吐槽居家辦公以來沒日沒夜,時刻被同事找。
輪到我了,我說我確診了。接著我就收到了一大堆的問題和反饋。S轉給我一篇關于新冠后遺癥的報道,還特意說明“并沒有開車,只是有求知欲”。北京的Y仔細地詢問我的癥狀,表示要給我寄一些藥品,還推薦了一款對治療咳嗽有利的設備;這讓我感動不已。
相比國內朋友的熱情和緊張,身處國外抗疫差生的朋友“冷漠”很多。對日本抗疫已經不再抱有幻想的Z的第一反應是:“你應該就免疫了吧”。在荷蘭讀書的T祝我多休息,自嘲說自己可能已經感染過又好了。
天氣預報很準確,傍晚果然飄起了雪。望著窗外寒風刮起的樹枝顫動,我又故作深沉了。我想念此時上海街巷溫暖的早晨、漢口江灘上的風、杭州斷橋春天下的余暉。雅典真冷。
手機又響了。在確診報告抵達后一個小時,我接到檢測機構打來的電話,確認我是否收到了通知。我說收到了,然后問他:“我現在陽性了,應該怎么辦?”
“不要擔心,好好休息。”電話里說,“會有XX機構聯系你的。”
我對這個機構名詞感覺很陌生,繼續問他:“大概什么時候聯系我?”
“三到四天。”
4
我沒有接到“XX機構”的電話,到現在都沒有。期間我只接到一個本地電話,3月10日,就是我收到檢測報告的第二天上午,一個女的在電話里自報家門,說她是Public方面的。我以為是昨天被告知的“XX機構”,趕緊問她有何指教。
她說,“你訂的書還需要嗎?我們可以盡快給你送過去。”
我想起來了,是兩周前在一家名叫Public的網站上訂的書。我說你們這幾天送來吧。
第二天,我收到了6本書。我遠遠地站著,打手勢,指示快遞員把書放在路邊的石墩上,我自己搬就好。我雖然有點虛弱,但拆快遞還是很有勁。這些書里有一本索福克勒斯的《忒拜戲劇集》,里面俄狄浦斯王的故事開篇就說,忒拜城遭遇了一場瘟疫。
現在我要找點事給自己。病癥初起的那天,也就是3月5日,我在市區買了兩本書。一本是我在舊書攤上買到的《月亮與六便士》,一本是牛津版的《戰爭與和平》。
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本書,我在15年前就讀過好幾遍,尤其是這本書的第五十章。那天晚上,我還把這一章念給我的埃及朋友聽,因為作者提到了發生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的一個故事。
至于《戰爭與和平》,對我而言是一座高山。這幾天,隨著俄烏局勢的發展,歐美出現了一種滑稽的抵制風潮,以至于米蘭的一所大學原本進行的一場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座也被取消。這讓我覺得,也許俄國人的書被下架也不是件太奇怪的事。于是,當我在書店看到這本紅色封面、牛津版、字典紙印刷的《戰爭與和平》時,想到最近發生的一些事,趕忙買下了它。
我好像特別會打發隔離中的無聊時光。前年此時,疫情第一年,我在杭州隔離的半個月,除了在線辦公,還讀完了一大厚本王爾德的小說和戲劇。去年8月,我在隔離的四個星期里,學完了《大家的日語》第二冊和半冊第三冊,以至于我解除隔離后特別懷念那一段時光。
未來至少一周,也許要兩周,我都沒辦法去學校上課。為了不讓課業生疏,我把那篇看病場景的對話,反復跟讀錄音,終于把它“熟讀并背誦”了。我看完了陳松伶在神仙打架的年代里主演的一部電視劇,追了好幾集穿墨綠色襯衫、盤膝而坐的主持人用低沉的嗓音、飽含深情地講解中國古代藝術的視頻。我又重新讀了《蒂凡尼早餐》的前面一小部分,把霍莉在家庭舞會中對“我”說的那幾句話讀得滾瓜爛熟。
還有點時間,我就胡思亂想。我以前很多次幻想過死亡之后會怎樣?這不免有一些矯情,但在中招之后,的確有人問過我,要是死在國外咋辦。我說,我倒是真的可以好好想想。
我沒有出現幻覺,就只是胡思亂想。在某個凌晨醒來的時候,我想如果我死了,被發現的時候大概是什么樣子?也許是連續不上課后,老師發來警告郵件仍然被我置之不理,之后怒氣沖沖去教務投訴,然后教務老師聯系不到我,大概在一個月后來踢門;也許是我連續拖欠水電房租,被中介警告說“您已經因逾期被罰款500歐”、“很遺憾您已經被罰款1000歐”、“經多次催促,我們仍未能收到您應繳付的租金,根據合約,您的租賃合同已經被強行終止”,隨后來踢門;也許是氣溫升高后,味道已經影響到了隔壁的情侶,他們怒吼著踢我的房門,用我聽不懂的希臘語斥責我不講衛生,幾天后發現全無效果被迫報警。
我的信用卡每個月還有幾項自動扣款,視頻、云盤、慈善捐款,賬單會被自動轉賬結清。如果這些企業和機構沒有早點倒閉的話,多年后我的余額會被逐漸耗盡,之后信用卡開始被計算利息、滯納金,留下一個惡劣透頂的信用報告,最后被銀行強制停用并威脅起訴。他們很快就會發現他們沒辦法把傳票送達,這真糟糕。
我又在迷迷糊糊中睡著了。
5
3月11日早上,我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在群山之間奔跑,但被一根繩子拉著。我氣喘吁吁,醒來發現睡衣扣子擰巴到了后背。
咳嗽似乎比昨日略有加重,而且還伴隨著胸腔的疼痛。我拿起手機,搜索“新冠、咳嗽、胸痛”等關鍵詞。一則貼士說,如果伴有胸痛就應該立刻去醫院;另一則貼士說,如果出現胸痛,不一定要立刻去,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果然凡事都有兩面性。
另一篇標題聳人,說如果感染了新冠,最好不要輕易服用這些藥物,否則……我趕忙點開,里面介紹了一些常用的消炎藥。我看到一個藥物的名字,恰好是老師介紹給我的,這讓我很放心。
這篇文章還附帶了一個擴展鏈接,介紹了血氧儀的使用。我點開看了一下,感覺很有道理。文章描述了血氧低的幾個癥狀,比如頭暈、饑餓感、行為不協調等,這些我好像都經歷過。
我突然意識到,我其實一直不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從沒有積極應對,發病三天才第一次測體溫,全憑僥幸。我此刻感到了一點心理壓力;如果說在我確診期間全無壓力,那是不可能的。這個時候恰逢國內防疫壓力驟增之時,而朋友的關心更令我感到需要認真對待這事。
發病的前幾天,我每天早晚各沖一片泡騰片,一共花費2.8歐元。一個朋友說我太草率了,“這是新冠,你不能就這樣對付過去”。我覺得很有道理,但我也不知道怎樣做才算重視。
我趕緊起床,吃了兩顆費列羅巧克力,接著下樓去買了一個血氧儀,30歐元。我需要確認一下,之前走路感覺有點飄,到底是因為沒吃飯,還是血氧低。我本來想買那個40歐元的,藥劑師勸阻了我,說這沒必要。我于是又在她這里買了一盒止痛藥和一盒泡騰片,又花費了5.3歐元。刷卡之后,我感覺踏實多了。
血氧測量結果是97%,正常范圍,我長舒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長舒一口氣的科學依據是什么,但的確感到輕松多了。為了讓它物有所值,我每天都會測兩次,到現在我看到它時,還會拿出來夾一下手指。只要看到正常閾值內的數字,我就很高興。
事實上,周日(3月6日)晚上開始到周二(8日)下午這一段時間狀況比較差之外,在機構檢測的正式報告下達當日,我感覺還好,至少,這個檢測是我步行15分鐘自行去做的。此后幾天,除了嗓子還有點不舒服,我覺得和平時差別已經不大,我又能滔滔不絕地講話了。
我之前惴惴不安等待的“XX機構”的電話始終沒來。按照當地規定,陽性后需要自我隔離5天。這期間,沒有“XX機構”搭理我,看來我只是他們確診統計中的一個數字。每天都有國內知情的幾個朋友來詢問我的進展,我有點愧疚,感覺給他們添了麻煩。
發病后的第7天是個周日,我感覺恢復的差不多了,再次進行了自測。樣本溶液經過字母T的時候沒有停留,劃過去了,留下一道紅線,陰性。
程序上,我需要做一個正式檢測報告來確認這件事,之后才可以返校上課。我停止了沖泡騰片,新買的止痛藥一直也沒有拆,也許留待下次。
為了增加點儀式感,我打開薄伽丘的《十日談》——講述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爆發時一群男女在郊外避疫期間的故事集——翻開第七天的第七個故事。這是一則發生在博洛尼亞的閨中秘事,粗俗又諧趣。我讀了兩遍。
我出門買了一張彩票,還是沒中,跟我病發那天一樣,仿佛這一周沒有發生過。
九派新聞特約撰稿 顧嘉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 頭發干枯毛燥很難受?快試試這些食物 可以滋養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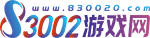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