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長(zhǎng)輩歸真了。他病了好幾年,昨晚到的時(shí)候躺在床上,喉嚨里只有“荷荷”聲以及痰在身處的咕嚕嚕聲,沒(méi)辦法說(shuō)話了,吸痰吸不出來(lái),太深了,用棉簽往里探不到痰,他搖搖手不說(shuō)話了。長(zhǎng)輩的老伴急哭了,說(shuō)“他不行了!”,像是對(duì)一件很在意的事表示失敗。我們勸她會(huì)好過(guò)來(lái)的,她說(shuō)不可能了。我爸給長(zhǎng)輩擦了眼淚,他側(cè)躺蜷縮著身體,枕著枕頭和自己的手,老伴輕拍著他告訴他所有人都盡職盡責(zé)了,“你很有福,三個(gè)孩子沒(méi)日沒(méi)夜的照顧你一年零四個(gè)月,還能怎么樣呢?”
我們把客廳的家具清空,柜子和沙發(fā)等在院子里堆積成山,下著雨,大雨點(diǎn)一直打我的后腦勺。客廳打掃干凈后把他放在中間。所有人圍在他身邊哭泣,長(zhǎng)輩老伴說(shuō)沒(méi)有呼吸了,大哭起來(lái),人們勸她說(shuō)還有,她說(shuō)“沒(méi)有了!”,那是4月12日11點(diǎn)52分。我說(shuō)叫阿訇,我們打電話去叫,打不通,阿訇睡了,于是騎單車(chē)去清真寺敲門(mén)。阿訇到了以后,穿著一件黑色長(zhǎng)衣,戴黑色清真帽,蹲在長(zhǎng)輩身邊,握著他的手放在自己懷里,側(cè)過(guò)身子貼到耳朵旁說(shuō)“我現(xiàn)在給你念經(jīng)文”,然后低聲開(kāi)始念誦。念完后沉默一會(huì),長(zhǎng)輩沒(méi)有心跳了,有人讓阿訇摸摸,阿訇不太懂,遲疑著去摸脈搏,脖子,大家哭了。
隨后他公開(kāi)念經(jīng),我們伸出雙手看著手掌,他念完后我們做洗臉動(dòng)作。我和表弟去清真寺抬了一張鐵床板,順便拿裹身的白布。回來(lái)后看了長(zhǎng)輩最后一眼,嘴巴左上方有兩個(gè)黑色的潰瘍,還保留看床邊來(lái)者的姿勢(shì)。蓋上白布后開(kāi)始守靈。長(zhǎng)輩的妹妹到了,哭的時(shí)候說(shuō)父母和兄長(zhǎng)都?xì)w真了,她活得太久了。給很多人打電話,通知,靠這種打電話通知訊息的活動(dòng),我們覺(jué)得很多人要來(lái)分擔(dān)了。一夜間很多老人來(lái)哭靈,長(zhǎng)輩的大哥在外地,疫情隔離來(lái)不了,他說(shuō)能來(lái),繞路,走“下面”,但最終沒(méi)能來(lái)。幾個(gè)小輩也因隔離無(wú)法到場(chǎng)。親族里幾個(gè)得力的親近中年男人到場(chǎng),很穩(wěn)重,開(kāi)始安排布置。
我們搬運(yùn)了家具、掃地和做了工作的男性去清真寺洗了大凈。漱口鼻三次,從頭洗到腳。清真寺的熱水很充足,只有淋浴,有十幾個(gè)公用拖鞋,我進(jìn)的洗澡間有兩瓶洗發(fā)水,在浴室一端的架子上掛了許多毛巾,浴室的所有東西都是家用款式,和營(yíng)利性的公共浴室不同。浴室燈光很暗,關(guān)上洗澡間的門(mén)后,洗澡間黑暗一片。洗完后穿上鞋,在夜里回長(zhǎng)輩家。客廳沒(méi)有裝門(mén)簾,白天會(huì)光線太足,所以臨時(shí)裝了門(mén)簾。
在長(zhǎng)輩身邊兩側(cè)鋪了白色被褥,我們跪或者坐在上面守靈。我自12點(diǎn)守到次日7點(diǎn),睡到11點(diǎn)又來(lái)。來(lái)后發(fā)現(xiàn)不是前夜人少安靜的場(chǎng)面了。下午運(yùn)來(lái)了透明靈柩,開(kāi)了冷氣。很多人來(lái)到,把院子和小巷擠滿了。人們本來(lái)在說(shuō)話甚至有人笑,“這是誰(shuí)家孩子?”、“小劉家兒媳來(lái)了”、“怎么不在這吃飯?馬上做好了”等等。有人抱著肩膀在墻邊討論事情,他們久不見(jiàn)了,趁此機(jī)會(huì)才聚聚。
前來(lái)見(jiàn)最后一面的客人來(lái)到后會(huì)哭一陣子,人們也立刻隨著震天的哭,像是《請(qǐng)回答1988》里那樣。
晚間我從7點(diǎn)50開(kāi)始守,兩邊的被褥上睡了除我以外五個(gè)人,我聽(tīng)見(jiàn)有人手機(jī)偶爾發(fā)出麻將的“吃”聲。我負(fù)責(zé)續(xù)香,也就是在靈柩前一個(gè)小碗,裝了花壇的土,燒一根香,燃盡之前再燃一根新香接續(xù)。續(xù)了大概50根左右。大人們?cè)谠鹤永锪牧艘灰梗蟾盼鍌€(gè)人,聊咖啡、打仗、過(guò)去。八幾年我爸開(kāi)貨車(chē),一次裝5噸貨,接到了60噸的單,于是雇傭了六個(gè)裝卸工在兩邊裝卸,他來(lái)回開(kāi)了12次。除去雇傭工人的幾百塊,他賺了很多,很快成了萬(wàn)元戶。
有幾年車(chē)一直在漲價(jià),他們一萬(wàn)多塊買(mǎi)的拖拉機(jī),開(kāi)了十幾年后賣(mài)了三萬(wàn)多塊。拖拉機(jī)第一次開(kāi)回家時(shí)大家都不會(huì)駕駛,請(qǐng)了某莊的人來(lái)開(kāi),一位舅舅。靈柩另一面有人打鼾和偶爾放屁。夜的初期人們說(shuō)加衣服、拿被子,我覺(jué)得沒(méi)什么,天氣二十多度,怎么會(huì)冷呢。結(jié)果到了凌晨很冷,我拿了棉睡衣和薄被子,側(cè)躺著盯著香的燃燒。
差不多十幾分鐘點(diǎn)燃一根新香。地上兩個(gè)打火機(jī),一個(gè)看上去很便宜,火焰平平無(wú)奇,一個(gè)看上去有點(diǎn)貴,不過(guò)也是塑料機(jī)身普通設(shè)計(jì),只不過(guò)火焰很沖,像是等離子光劍。兩點(diǎn)以后我閉著眼打算睡覺(jué),怕自己睡著沒(méi)人續(xù)香,但不想叫醒別人。好在我半夢(mèng)半醒中維持了十幾分鐘續(xù)一次香這件事沒(méi)有中斷。
在五點(diǎn)我表弟醒了,我回家睡覺(jué)。睡到8點(diǎn),全身酸疼,惡心,不想喝水,不想洗大凈,因?yàn)槔浜屠邸N以诩依锷嘲l(fā)查了古蘭經(jīng),說(shuō)“不洗大凈者不要去葬禮,除非洗了小凈”,于是我洗了小凈,手,手肘,臉,耳朵,漱口鼻等,坐在馬桶上脫鞋洗腳。
到長(zhǎng)輩家時(shí),運(yùn)來(lái)了一個(gè)水柜,白色塑料外殼,里面的水泛白,像是肥皂水。那是我小時(shí)侯見(jiàn)到清真寺阿訇的孩子去拉水用的。有三個(gè)暗金色的壺,阿訇用它清洗遺體,白布遮住隱私部位,其余身體黃色枯瘦。人們隔著客廳門(mén)簾用三個(gè)小壺傳遞水。一些男人在客廳里站著默哀。由于儒家習(xí)俗的傳染,女人們不能進(jìn)去,都在客廳門(mén)口站著,院子外小巷子里依然站滿了人。男的帶小白帽,女的帶白色蓋頭,所有人的幾乎都是長(zhǎng)輩家人買(mǎi)來(lái)發(fā)給的,很少有自己帶。自己家里帶來(lái)的小白帽、蓋頭會(huì)有幾何花紋和色彩,做工精細(xì),甚至有金線。我們買(mǎi)來(lái)發(fā)給人們的是純白色的。
洗完后還有最后一項(xiàng)儀式,人群進(jìn)去繞一圈瞻仰,遺體被白布裹身,只能看到面容。繞一圈后出來(lái),哭聲很大。幾年前在東關(guān)大清真寺的天井里我第一次見(jiàn)到這種儀式,我太爺爺。人們自正門(mén)魚(yú)貫而入,圍繞經(jīng)過(guò)遺體一周,自正門(mén)出去,隊(duì)列很長(zhǎng)。
期間的議論:
在齋月中歸真是好事,可以上天堂。
從病中解脫是好事,不用再受苦了。
舅媽的娘家人囑咐舅媽?zhuān)驯淅锶镅蛉饽贸鰜?lái)化凍,夜里要睡覺(jué),明天要做飯等等。(長(zhǎng)輩家人要招待所有來(lái)客,但不擺席,只是幾鍋酥肉,一人一碗)
我認(rèn)為歸真是件中性的事,打比方說(shuō)一個(gè)千年結(jié)束我們會(huì)殊途同歸,連同現(xiàn)在未出世的幾十代人,都會(huì)是走完這路的人,躺在黑暗的地下或者付與劫灰,沒(méi)有意識(shí)的失去顏色的肉身在地震或者俗事中被顛來(lái)倒去。所以在守靈時(shí)對(duì)近在咫尺的遺體并無(wú)特殊感受。是我缺乏睡眠的關(guān)系,也是我的感情麻木。不能說(shuō)是“愛(ài)的方式不同”,如果我自己到這一步估計(jì)會(huì)哭,我沒(méi)法和長(zhǎng)輩感同身受。我表弟也沒(méi)有哭,他在一個(gè)時(shí)刻磕了頭,我守了一夜靈,我不喜歡和人說(shuō)話,所以是靜默的守的。
————————————————————————
12日11點(diǎn)歸真,13日停留一天,14日也就是今天上午下葬。“差十分鐘,算是第一天”、“一切從簡(jiǎn)”。
運(yùn)送遺體的車(chē)后跟著一支車(chē)隊(duì)。我和兩個(gè)老人坐在我爸車(chē)上,一個(gè)戴著黑底綠線小白帽,無(wú)須,皮膚黑紅,一個(gè)留著山羊似的白色胡須和鬢角,像是頭發(fā)濕了的那種形態(tài),都一綹一綹的,很枯燥。其中一人在路上指著車(chē)隊(duì)后面一輛車(chē)說(shuō)“那是蘇大胡子的車(chē)”,我才知道這位大胡子不是蘇大胡子,我一直認(rèn)為他是。
去了祖墳處。車(chē)隊(duì)特意繞了祖宅一圈,因?yàn)殚L(zhǎng)輩在病中一直想回來(lái),但不是住院就是疫情,沒(méi)有機(jī)會(huì)回祖宅居住。前后兩進(jìn)院子,前面的院子更古樸,后面的院子是八幾年修的,一個(gè)老人在后座贊嘆“當(dāng)時(shí)這是最高級(jí)的院子,明三暗五,喲,真不錯(cuò),你看看”,另一個(gè)老人點(diǎn)頭同意。
“奧,你們帶他繞一圈。”老人說(shuō)。“你們守了兩夜?真……(孝順?或者用功)”
我們?cè)谔镩g行駛,麥子長(zhǎng)成了,只是還綠著。放倒了一片長(zhǎng)方形作為人群的通路。墳?zāi)故?3日建造的,挖掘機(jī)和泥瓦匠的功勞。本來(lái)打算十天前就找人建造,因?yàn)楫?dāng)時(shí)長(zhǎng)輩就不怎么吃東西了。“當(dāng)時(shí)該打電話給這邊的人,有兩個(gè)伯伯,在這一片很有影響力,可以安排,辦的太晚了,但沒(méi)有出疏漏還是可以的”。13日凌晨人們?nèi)プ鎵灴吹牡胤剑缓蠼腥藙?dòng)工。
墓室里面有很大空間,想下去要走三級(jí)階梯。我太爺爺?shù)哪故抑杏邪籽L(zhǎng)輩的墓室我沒(méi)在正面看,所以不知道里面的情形。老人們?cè)陔A梯上面的兩旁舉著一張寫(xiě)滿了金色經(jīng)文的布,由親近的子嗣途徑經(jīng)文布下方,將白布裹身的遺體送進(jìn)去,他們把白鞋脫在階梯上,在里面布置了一會(huì)。
阿訇來(lái)得很晚,我們?cè)诼飞辖o他打了電話,他卻還在清真寺門(mén)口站著。小路上一個(gè)親戚老人說(shuō)“我去叫他”,于是跑著去叫。
隨后開(kāi)始砌磚,老人回來(lái),說(shuō)阿訇朝他擺擺手,大概是知道了一會(huì)就來(lái)。來(lái)了大約四五十個(gè)人參加儀式,我奇怪的是竟然有女人在,還不戴蓋頭,那為什么不許家里的女人來(lái)呢?人們開(kāi)始鏟土,同時(shí)有好幾團(tuán)泥土在空中飛,一個(gè)老人說(shuō)“他要知道這么多人來(lái)看他”,我看田間狹窄的土路上不停有孤單的男人來(lái),都戴著黑色的清真帽,我認(rèn)為其中兩個(gè)人是阿訇,都猜錯(cuò)了,在我放棄看土路時(shí),阿訇在一個(gè)我觀察地上枯草的時(shí)候來(lái)了,拿著一個(gè)大音箱,開(kāi)始唱經(jīng)。聲音有點(diǎn)“如泣如訴”,哀怨的歌聲,但只是幾個(gè)瞬間,本來(lái)唱經(jīng)就是這樣。
五把鐵鏟,幾個(gè)老人高喊“換一換,都鏟幾下!”,我聽(tīng)成呼喚的喚,打算大家開(kāi)口我再開(kāi)口,結(jié)果是我想錯(cuò)了。大家開(kāi)始輪流使用鐵鏟,但許多人沒(méi)有鏟土,所以有人高喊“怎么不換?都是來(lái)幫忙的,換一換!”
一個(gè)人突然轉(zhuǎn)頭向另一個(gè)人去,并且握手,小聲說(shuō)“舅舅,我剛看見(jiàn)你在”。
我踩在隔壁的墳的“山腰”上看地下階梯的情形,所有人連同我圍繞地下室一周站著。來(lái)的土路上遍布黃色的離根稻草,小包的空化肥袋子,失去顏色的殘存塑料布,綠葉,樹(shù)枝,青綠色的麥穗等。隔壁的墳上都是純白的草的遺體,沒(méi)有顏色,分解前夕的狀態(tài),同時(shí)身邊還有許多青綠色的同類(lèi)很有生機(jī)。有一種草葉像是花或者四葉草,綠色被暗紅色沾染,幾條平行的土路兩旁種的都是楊樹(shù),路中間是面積很大的麥田。遠(yuǎn)處有淡紫色、淡粉色的樹(shù),桃花或者什么,它們后面是一處鐵路。
我找一個(gè)人要鐵鏟,他干得熱火朝天,沒(méi)理我,我叫他,然后伸手,有點(diǎn)尷尬,隨后他發(fā)現(xiàn)了我,讓給我了。我鏟了大概十幾下,他戳了一下我的背,又要回去了。填平以及整理了墳包。回去后發(fā)現(xiàn)車(chē)的引擎蓋上停留一大片蒼蠅,墳?zāi)股弦灿猩n蠅。楊樹(shù)皮都是灰色的,很多塵土。
回去的路上的議論:
某長(zhǎng)輩的墳?zāi)乖诹硗庖粋€(gè)城市。“他妻子在這里埋,他在那邊,這邊一個(gè)單身,那邊一個(gè)單身?”一個(gè)老人問(wèn)。“不是,他多少年前還有一個(gè)妻子,給他生了一個(gè)女兒,他們倆在那邊埋,是祖墳。”另一個(gè)老人回答。
田間很多墳?zāi)埂!斑@個(gè)是誰(shuí)的?”“他們小舅的。”“這個(gè)是埋的誰(shuí)?”“xx的嫂子。”
“墓室可以夫妻兩個(gè)同時(shí)辦好,省錢(qián)。”老人說(shuō)。“你想嚇?biāo)浪ㄩL(zhǎng)輩老伴),她很怕死,不能提這件事,現(xiàn)在就辦一個(gè)。”一人答。
“當(dāng)天晚上都在哭,他們哭他們的,我摸我的,先摸手腕,沒(méi)有脈搏了,又摸心跳,沒(méi)有心跳了,又摸脖子靜脈,沒(méi)有了,那那只能……那是十點(diǎn)五十。”
四個(gè)親屬在另一處田間墳?zāi)古圆⑴拍В以谶h(yuǎn)處時(shí)看見(jiàn)了,像是田里一條微粗過(guò)田壟的黑線。其中有一個(gè)我的舅舅,四十多歲了,秘密著身體探進(jìn)車(chē)窗找我爸要煙。從小我們玩各種冒險(xiǎn)違禁的游戲,他還在玩,低聲顯得很俏皮,他留著山羊胡子的雛形,長(zhǎng)的很像八幾年的搖滾明星,或者房祖名。做派也像,有種相對(duì)而言長(zhǎng)相好者(同時(shí)經(jīng)濟(jì)狀況不錯(cuò))特有的撒嬌意味,穿著黑色皮衣,戴著自備的有花紋的禮拜帽。
路上是常見(jiàn)的灰色天空,低伏的城郊建筑。很多小葉樹(shù),葉子像是向外掙脫成功的瞬間定格了,不像固定在樹(shù)枝上的樣子。回來(lái)后葬禮算是告一段落,我回家睡覺(jué),人們?cè)陂L(zhǎng)輩家吃中午飯,回族的燴酥肉。睡到下午,有個(gè)微信微粒貸的騷擾電話,開(kāi)頭讓我以為我欠錢(qián)忘了還了,聽(tīng)明白后我掛斷了,還有個(gè)快遞到了的電話吵醒我,我說(shuō)放在xx超市,我回頭去拿。下午六點(diǎn)四十我又去了長(zhǎng)輩家,一個(gè)儀式,聽(tīng)著是“叫天子門(mén)”,就是呼喚一場(chǎng)。結(jié)束后我去拿快遞,結(jié)果沒(méi)有找到,繼續(xù)回來(lái)睡覺(jué)。
——————————————————————
人們互相同化。表示哀思也要成群結(jié)隊(duì),大多哭聲都震天響,儀式化,說(shuō)停就停,葬禮沖淡哀思,撫慰人心,長(zhǎng)輩的大兒子說(shuō)“我送煙要買(mǎi)好的,辦的最好”,大家集中注意力做應(yīng)該做的事,個(gè)人多愁善感的情緒被壓制了。通過(guò)勞碌解釋獨(dú)處時(shí)會(huì)遇到的悲哀,邀請(qǐng)來(lái)的眾人更是共同承擔(dān)了離別的感情重量。我第一天很驚訝阿訇姍姍來(lái)遲,沒(méi)有解決長(zhǎng)輩臨終的心情,他當(dāng)時(shí)流眼淚很不舍。但下午回憶,阿訇在最后幾分鐘里貼得很近(半跪著,上身傾過(guò)去)握著長(zhǎng)輩的手念經(jīng)。講復(fù)活和靈魂不滅需要思考,而且歸于饒舌,但握著手,念經(jīng)文提供的是切實(shí)無(wú)法懷疑的“我被宗教事務(wù)者(阿訇)握著手”,“他在替我念誦經(jīng)文”等,這不是日常的事,是宗教事務(wù),真正的有關(guān)于一人、阿訇和神之間的有關(guān)于生與死的私人事務(wù),提供神秘的安心。比講神學(xué)然后思辨這種日常領(lǐng)域的事要好。
在阿訇沒(méi)來(lái)時(shí)我想跟長(zhǎng)輩說(shuō)還會(huì)再見(jiàn)的,很多年以后,如果信教的話,就信會(huì)復(fù)活,還會(huì)再見(jiàn)的。那時(shí)候沒(méi)有現(xiàn)在的很多思考了,肉身和日常的心酸,比如過(guò)去的日子都沒(méi)有意義了,不需要哭。但我沒(méi)說(shuō),氣氛不允許人講這些話。
長(zhǎng)輩的所有衣服被扔了,怕遺孀睹物思人。
女婿:老頭對(duì)我不錯(cuò),八幾年。(他和長(zhǎng)輩女兒結(jié)婚,他的母親不同意,身為婆婆和兒媳吵架。長(zhǎng)輩沒(méi)有介入,不是讓雙方家族陷入無(wú)人承擔(dān)責(zé)任的瘋狂爭(zhēng)吵,而是默默支持女兒。最后女婿和自己母親分家,支持了自己的妻子。)
長(zhǎng)輩是典型穆斯林老頭的樣貌,但沒(méi)有胡子,下巴總剃的干干凈凈,他的爸爸不是,他爸爸有一副山羊胡子。長(zhǎng)輩瘦弱,不常帶小白帽,常穿老式西服和白襯衫,寡言少語(yǔ),不茍言笑,哭和笑都很沉默,吃飯不說(shuō)話,掉飯粒要吃掉,不講究吃穿;戴眼鏡,干凈肅穆。幾乎沒(méi)見(jiàn)過(guò)他去禮拜,向來(lái)不麻煩誰(shuí),最后病了讓幾個(gè)孩子照顧了很久是例外。得病初期長(zhǎng)輩曾經(jīng)整夜枯坐,大概在想事。在住院時(shí)被折磨的放棄了個(gè)人衛(wèi)生,膿和血滿身都是,護(hù)士不負(fù)責(zé)清理,扯皮了幾次。我守靈的時(shí)候躺在兩面墻夾角,左邊這面上面掛著一幅畫(huà),畫(huà)框和玻璃看著很沉重,我小時(shí)侯扔沙包砸下來(lái)過(guò)它的前任,彼粉身碎骨,嚇得長(zhǎng)輩出來(lái)看我們,腳步很輕,波瀾不驚又回去了,好像責(zé)備了我們,但沒(méi)印象。我怕這幅畫(huà)再跌下來(lái),于是用胳膊肘護(hù)著額頭躺著。
另一面墻上掛了七八個(gè)畫(huà)框,有漢語(yǔ)對(duì)聯(lián),“尊天道認(rèn)主拜主,尊人道孝敬雙親”,有清真字,我看清真字比漢語(yǔ)少了一個(gè),應(yīng)該是“天道”和“人道”都各自是一個(gè)單詞?四個(gè)對(duì)聯(lián)玻璃框中間是天房和塔的幾何圖畫(huà),它們上面是兩個(gè)橫聯(lián)。寫(xiě)的字和畫(huà)的線都看得出是八幾年、九幾年手工的,有些地方不直,顏色濃淡不均勻,全是大方嘴筆畫(huà)的,點(diǎn)是菱形,各自形態(tài)不一。這些對(duì)聯(lián)也是長(zhǎng)輩的遺物,這間房子,一起住的小兒子夫婦,到處都是長(zhǎng)輩的意志存留著。雖然最后幾十年大兒子接過(guò)家業(yè),長(zhǎng)輩收入低微,但舊物當(dāng)初都是他買(mǎi)來(lái)的。
長(zhǎng)輩眼睛一直很有神,即使在醫(yī)院里,老一輩把這些基礎(chǔ)的事當(dāng)作天經(jīng)地義,放棄都放棄不掉。“不管我心情多差,別人來(lái)了我要整理精神”。最后一夜眼神呆滯無(wú)光了,這是大家認(rèn)為“看著整個(gè)人都不一樣了”的理由。不管是靈魂不滅等待復(fù)活還是肉身變?yōu)閯?dòng)物植物的來(lái)源,意義永遠(yuǎn)存續(xù),因?yàn)榇嬖谝呀?jīng)發(fā)生了。在回來(lái)的路上我很想喝糖水,就去買(mǎi)了一聽(tīng)黃色芬達(dá)和一瓶西瓜味芬達(dá)。對(duì)我而言,“開(kāi)始了”,歸真蔓延到了長(zhǎng)輩那一代,而不是久遠(yuǎn)的出生于民國(guó)初年時(shí)的太爺爺歸真那樣充滿了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臍夥眨瑤缀鯖](méi)有人哭,因?yàn)樗詈髱资晟詈艹良庞拈e,和子嗣沒(méi)有多少交流;不像長(zhǎng)輩這樣活躍的日子歷歷在目,他翻蓋自己的老宅才三十多年而已。
[責(zé)任編輯:linlin]
標(biāo)簽: 請(qǐng)回答1988 搖滾明星
相關(guān)文章
-

天天觀熱點(diǎn):究竟是徒有其表,還是內(nèi)有乾坤——聊一聊《瞬息全宇
-

環(huán)球播報(bào):【童話/寓言】解藥
-

天天觀點(diǎn):【丑小鴨】
-

全球微動(dòng)態(tài)丨【故事新編】圣誕老人的禮物
-

每日觀察!森林幻想曲
-

焦點(diǎn)消息!在失眠的夜晚,我又打開(kāi)了《糖豆人》
-

視焦點(diǎn)訊!“我們的幸福生活” 短視頻征集展示活動(dòng)正式啟動(dòng)
-

今亮點(diǎn)!【睡前故事】海的女兒之人魚(yú)的謊言
-

當(dāng)前熱點(diǎn)-【童話新編】小美人魚(yú)
-

【全球熱聞】翻譯翻譯,什么叫情書(shū)?情書(shū)就是翻一翻……
-

【環(huán)球報(bào)資訊】小紅帽的故事
-

天天實(shí)時(shí):不是豪門(mén)媳婦嗎,怎么又出來(lái)掙錢(qián)了?
- 1 國(guó)家藥品集中采購(gòu)倒逼藥企殺價(jià)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jī)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guó)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qián)”活動(dòng)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xiě)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chēng)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lái)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zhuān)用車(chē)廂 到底有無(wú)必要?
- 10 教練長(zhǎng)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zhǎng)實(shí)名舉報(bào)
- 1 國(guó)家藥品集中采購(gòu)倒逼藥企殺價(jià) 行業(yè)正在經(jīng)歷洗牌
- 2 山東掃黑除惡成績(jī)單發(fā)布 查扣資產(chǎn)219億余元
- 3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guó)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4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qián)”活動(dòng)
- 5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6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xiě)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chēng)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lái)了
- 7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8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9 女性專(zhuān)用車(chē)廂 到底有無(wú)必要?
- 10 教練長(zhǎng)期猥褻未成年球員 多名球員家長(zhǎng)實(shí)名舉報(bào)
- 房地產(chǎn)業(yè)或迎融資"緊箍咒" 多家房企積極表態(tài)
- 華為春季新品發(fā)布支持VR直播 供應(yīng)鏈國(guó)產(chǎn)化引關(guān)注 5G手機(jī)密集發(fā)布
- ofo上線新套路:想拿回99元押金需先消費(fèi)1500元 上線“天天返錢(qián)”活動(dòng)
- 中央軍委訓(xùn)練管理部四部門(mén)聯(lián)合印發(fā)《著裝辦法》退役軍人可以在公開(kāi)場(chǎng)合穿軍裝了
- 90后博士獲聘高校教授 曾每天16小時(shí)泡在實(shí)驗(yàn)室
- 河北一法官在家寫(xiě)判決時(shí)身亡 人社局稱(chēng)不是工傷 法院判決結(jié)果下來(lái)了
- 85歲老黨員不顧危險(xiǎn)跳水施救82歲落水老太
- 水下15米致命玩笑 兩游客菲律賓潛水時(shí)氣瓶被惡意關(guān)閉
- 妻子在酒吧被騷擾 丈夫暴揍對(duì)方致輕傷被判刑
- 六大關(guān)鍵詞讓你了解蘋(píng)果新品發(fā)布會(huì)
- 加密貨幣轉(zhuǎn)正!多米尼克立法確認(rèn)波場(chǎng)系代幣為國(guó)家法幣
- 蘋(píng)果今天發(fā)布了 Safari 技術(shù)預(yù)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fā)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cái)年第三季度財(cái)報(bào)-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fā)布會(huì)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kāi)-焦點(diǎn)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cái)年第三季度財(cái)報(bào)-全球今亮點(diǎn)
- DLSS 功能測(cè)試已支持英偉達(dá)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shí)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zhàn),雖然是個(gè)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jī)會(huì)-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gè)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qián)?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zhì)疑,“無(wú)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dòng)態(tài)
- 港星罕見(jiàn)合照,周潤(rùn)發(fā)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wàn)分,情懷爆棚-視焦點(diǎn)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guó)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lái)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méi)緩過(guò)來(lái)-全球簡(jiǎn)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dòng)車(chē)前五,年出貨量超過(guò)1000萬(wàn)-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diǎn)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tái):排名中國(guó)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diǎn)日?qǐng)?bào)
- 馬斯克稱(chēng)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wàn)億美元-環(huán)球觀天下
- 高等數(shù)學(xué)(上)習(xí)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diǎn)上線 山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zhuǎn)函數(shù)-當(dāng)前要聞
- 鄉(xiāng)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kāi)啟農(nóng)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jié)對(duì)共建助力新時(shí)代文明實(shí)踐
- 植宗山茶油發(fā)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wú)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yíng)養(yǎng)豐富哦~
- 金秋時(shí)節(jié)正是吃板栗的好時(shí)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dāng)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mén)看點(diǎn)
- 林志穎妻子回應(yīng)6歲兒子車(chē)禍后第一句話,聽(tīng)到真相時(shí)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guó)》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huán)球報(bào)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ài)為營(yíng)內(nèi)容大變買(mǎi)個(gè)ip網(wǎng)劇套原創(chuàng)劇利用書(shū)粉基礎(chǔ)宣傳-全球聚看點(diǎn)
- 蘇感加倍來(lái)襲,養(yǎng)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dú)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yù)售日10月24日進(jìn)行淘寶直播首秀-環(huán)球新資訊
- 養(yǎng)生俗語(yǔ)“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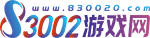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píng)論員文章
評(píng)論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