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二,慣例是川里人家上墳掃墓的時節,然而這習俗似乎僅在川里這一片地方,隔河的寬渡小鎮與左近的鄉里都只講究年前二十九去一次,再去便要等到清明時節。
這天我起的很早,天方蒙蒙亮,我便從被窩中爬起,然而父母都比我起得更早,在我起來之前,父親就已經將院子拿笤帚掃了一次。
母親知道我們今天要去祭祖,也及早開始備置上供用的各項祭品,片了一小盤豬肉,削了幾顆蘋果,裝了幾袋面包,忙忙碌碌半小時,一切都已備置妥當。
祭品中還缺一小瓶白酒,母親給了我五塊,叫我去家門外不遠處的雜貨鋪去買。
我領了錢走出門,買完酒回來時,正聽見母親對父親喊道:“葉群,你非要正月就去蹲個局子是不是?”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悚然一驚,趕忙上前聽緣由,最終卻是哭笑不得。
原來是父親喜歡熱鬧,往年正月出門圖個儀式感,總要在院里放個二踢腳再走,可今年川里政府下了禁煙花的嚴令,連往年公家經營的雜貨公司煙花銷售點都已經被關停,如果偷偷放炮被派出所聽見炮聲,不免要被拉走拘留兩天。
然而父親是個性子很倔的人,同母親爭執不下之后,見我回來卻是眼前一亮,忙喊道:“雙子,你媽牛的不行,不想給爹找炮放,你去給爹找去。”
我笑著搖了搖頭,道:“爸,你還是聽媽一句勸吧,今年是真的不能放這個炮,你想放咱們下午回來以后去塬上放去。”
“哪來那么多破講究!”父親生氣道,“你們娘倆合起伙來欺負我,我自己去找去。”
于是他大踏步朝著屯了往年留下的一點煙花的側窯洞走去,只留下我和母親面面相覷,無奈地笑了起來。
不多時,他便拿著一個二踢腳從窯里走了出來,一直走到院墻旁邊,把二踢腳放下,從懷中掏出一盒煙,拿出一根點著抽了起來。
白色的云霧籠罩了他的身形,他看起來似乎有些猶疑,俯身把二踢腳重新攥回到手中后,他反復揉搓著炮捻子,就這樣定定站了許久。
直到一根煙全部抽完,他也再未有任何動作。
“他不會放的。”母親似乎早已預知結果,沒有和我一樣傻傻站在院里看父親接下來的動作,而是早早提了那一小瓶白酒回家打包供品去了。
我看著父親頭上的云霧消失,他長嘆了口氣,將煙頭彈到一旁。
“算了,不讓放就不放吧。”他這樣說著,把二踢腳收回了自己兜里,回頭看向我,“看什么看,傻小子,準備起身了,去跟你媽拿東西去。”
我忙收回視線,點了點頭,回身到家中,只見一袋供品早就已經裝好放在茶幾上,母親正在餐桌旁看著手機中的直播。
“就那一袋。”母親指了指茶幾上的東西,“你爸他沒點那個二踢腳吧。”
“沒點。”我回答道。
“那就好。”母親繼續看向手機,似乎無事發生。
我提了供品走出門外,見到父親正站在院門口等我,于是趕了上去。
我們二人并行走著,我還聽見他在嘴中嘟囔抱怨著。
我察覺到父親有些不快,忙轉移話題道:“今天是正月初二,咱們等下去買黃紙和信香,不知道街上的攤子開不開。”
父親沉吟片刻,答道:“開著的,每年都開著的。”
許是因為川里的習俗原因,嗅覺敏銳的商販們并不會錯過這份賺錢的良機,正月也并不休息,父親剛說完,我便看到了一個小攤,上面擺滿的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走到攤位前,攤販熱情推銷起來:“我們這的紙錢面額川里最大,包你家祖先人人滿意,來年好好庇佑家族。”
父親聽了這話卻是微笑起來:“給老人們每年祭拜看的是心意重不重,紙錢大小這種事情,那也不過是你們往上去印的一個數罷了,不過我也真的希望如你所說,老人們泉下有知,好好照顧這些后人們。”
“那是,那是。”攤販忙點了點頭。
“好,就這些東西,你清點一下。”父親挑好了貨品,遞到攤販手里。
“兩捆信香,一扎黃紙,三捆紙錢,一共八塊五毛,收好。”攤販迅速點了父親挑的貨品,給出了報價。
父親把錢遞了過去,攤販把東西一裝,送到了父親手里。
我們二人轉身離去。
“你們慢走。”身后的攤販招呼道。
我從父親手里接過祭品,我們二人向著父親車的方向走去。
父親的車停在外街,我們要去的地方走里街要近一些,于是上車之后,父親開始把車向著里街開了過來,從作為里外街通道的寬巷繞過來后,一尊碩大的金屬雕像映入眼簾。
上面寫著大大的銅吳城三字,每次經過這尊塑像,我總不免多看上幾眼。
我們這里地方雖小,但稱號卻并不含糊,一直以銅吳城自居,吳城是地名,銅是封號,但我總覺得這篇土地似乎跟銅的關系并不算大,也并非盛產銅礦,也并非與銅有歷史淵源,于是從前一直好奇這名字的來由,但這幾年塬上卯上逛多了,我大抵明白了這里的銅所象征的不是一個歷史概念,也非一種特色產物,而是一種自然風貌,是黃土高原色彩的真實寫照。
不多時,車便走到了中心廣場,父親要下車再去買些東西,我便停在車上等待。
這時,我看見車外有一個奇怪的人影,他跌跌撞撞奔走著,似乎是喝醉酒了一樣,走著走著忽而摔了一跤,我見狀想下車去扶他,但還未等我有任何動作,他就又爬了起來,繼續向前走去。
父親買完東西回到車上,我向他問起了方才看見的奇怪人影,父親卻一臉茫然,并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疑惑道:“正月月初早上能喝成這樣,我還真不認識這么一號人。”
我見這個問題無果,也便不再追問。
走到縣教研室下方的斜坡那里,父親把一個伯伯和一個堂兄捎上了車,他們和我們此行的目的地相同,在宗親關系上,他們是我家大爺爺那一支的后人,這位伯伯自小同我父親相識,已有五十余載交情。
他對我的近況十分關心,卜上車便開始問東問西,我一一招架著他的問題,只感覺對他的熱情有些左支右絀,應付不來。
車子再向上走,拐過幾個橫彎,不多時便到了地方。
我們下了車,把東西從后備箱里取出來,朝著面前的一個土坡走了過去。
才走兩步,只見父親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早已同我的另一位堂兄一塊在前面等候多時。
父親見大伯手里提著不少東西,忙對我使了個眼色,我馬上會意,上去主動幫大伯提手中的東西。
大伯笑著對我點了點頭,把手中的東西交給了我,我和兩位堂兄一馬當先,走到了隊伍前頭,三位父輩則在后方慢慢走著,互相敘著年節間的趣事。
過年那兩天川里下過雪,城里頭人煙多的地方雪早便化開,但這墳場位居深山里,正月的日頭又不算太烈,因而前頭的土坡上還有不少積雪,我們在積雪中走的十分小心,拖著艱澀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前方。
幾分鐘后,長路終于到達盡頭,將手中的祭品與供品放到旁邊紅磚搭成的一方小臺上后,眾人站定下來。
父親把一沓黃紙交到我手里,讓我往各個墳前散紙,七個墳冢,一共是自爺爺一輩向前的三輩人。
最前方還有一個小小的土家,象征著對于土地神的尊敬和供奉。
在每一個冢的土堆上挖一塊瓷實的土拍在黃紙上,將各個冢上都拍滿黃紙,這項任務就結束了。以往的黃土稀松不堪,想找一兩塊能用的土都十分不易,這次落完雪的黃土十分濕潤,稍微抓一抓便變得瓷實,所以這項任務完成的比以往快了許多。
將最后奶奶的墳塋上拍完黃紙后,我看著前頭仍在忙碌的眾人,又過去幫了些忙。
所有準備都妥當之后,我們從土家開始拜祭前人。
眾人也不管膝蓋臟不臟,都直接在黃土上跪了下來,大伯捻了三柱香點著,插到靈牌前頭,父親從供品中掏出散碎的豬肉與面包丟在靈牌旁邊,另一位伯伯點了幾張白紙燒完,我們便對著靈牌磕頭,三下叩首之后,起身開始拜祭余下的墳冢。
所有流程,不一而足。
如此一個小時左右,終于到了奶奶的墳冢前。
每一次到奶奶墳前,父輩們都會有萬千感慨難以言盡,這位偉大的女人在很早便失去丈夫,以一己之力拉扯六個兄弟姐妹長大成人,最后卻在終于能享福的年紀早早離世,因此父輩們一直感到對她有所虧欠。
“說實在話,咱爸離開的太早了,我對他的記憶都已經模糊了。”跪在奶奶墳前的大伯嘆道。
“咱爸離開的時候大姐也才十六七歲,咱們幾個更小的小孩也確實沒有辦法記的太清楚。”父親同樣嘆了口氣。
“咱媽真的太可惜了,勞苦一輩子,老二你剛把房子蓋起來置辦好,她住了還沒半年,人就走了。”大伯一邊往酒盅里倒酒,一邊感慨著世事無常。
“后人就是感到生前有虧欠,死后才要加倍好好拜祭,老人們眼睛一合上,實際上就啥也不知道了,她哪管你拜不拜祭的,但是咱們不能不來,這是彌補生前的欠缺,是義務,也是責任。”父親點燃了紙錢,怕濕氣太重燃燒一半火滅了,用棍子翻攪著。
“對,葉群你說得對,這是義務,也是責任。”大伯點了點頭。
我聽著父親的話,陷入了沉思之中,我一直認為這每年都要進行多次的祭拜,是父輩們迷信觀念尚未消去,為了求個心安才進行的一項活動,但這時才知道父輩們這一舉動顯然并非是封建迷信的遺留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唯物者,在清楚認識到死亡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后,依舊堅決進行的一項義務。
我在想,生活在這片黃土上的人們最初或許就是懷抱著這樣的義務感與責任感,將這項儀式繁瑣準備復雜的祭禮不斷傳承下來,直到我這一輩,直到下一輩。
奶奶的墳冢拜祭完成后,我們便要起身離開了。
這時,大伯家的堂兄掏過來一掛鞭炮,打算把這掛鞭炮放了。
父親見狀連忙制止,道:“小濤,這倆天不能放炮,川里有規定。”
堂兄笑了笑:“沒事,二叔,我早就打探清楚了,這塊是準放區,可以放。”
父親這才松了口氣。
大伯轉頭看向父親,問道:“老二,你這次沒帶炮上來?”
父親神秘一笑,從懷里摸出來那個沒有點燃的二踢腳,擺在地上,點了根煙。
大伯也同樣笑了:“媽以前過年最愛看放炮,自己膽子小不敢放,你膽子大,也愛放炮,媽每一年都讓你來放,上來看一次媽,沒有你給她去放個炮,也不太圓滿。”
父親聞言沉默了,將燃著的煙頭貼在炮捻子旁邊,只聽見“嗤”的一聲,父親連忙跑開,一聲巨響震蕩在山谷之中。
硫磺獨有的硝煙氣味飄揚開來,淺藍色的煙霧彌漫在空中,這時塬上起了一陣怪風,帶著這股煙霧自西向東迅速飄遠,我凝視著山谷的遠方,只覺得在今天的日頭照射下,那千溝萬壑的金色大地好像熟銅澆灌而成的模具一樣美麗,這自然的偉力構造而成的奇異土地,確實擔得起銅城的名號。
當我回過神來時,父親他們已經走到了半坡處,我把身旁的籃子一提,趕緊追了上去。
后記:回程路上,我記起了在廣場看見的那個奇怪的人,想著以兩位伯伯的閱歷豐富,說不定能夠認識那個人究竟是誰,于是我把疑問拋向了兩位伯伯。
大伯一拍腦門,快速想了起來:“噢,是廣場那個理頭匠。”
“什么理頭匠?”父親也來了興致。
“那人叫老柱,也算吳城川里街頭的一個奇人了,早上理發下午喝酒,每天如此從不間斷,只要兜兜揣著一毛錢,他都一定會去買酒喝,所以幾乎從來沒有積蓄。”大伯頓了頓,又道,“這人有一個獨生女,前兩年已經出嫁了,他女兒嫁出去以后這人人老心不老,調戲人家有丈夫的女人,被人丈夫打了一頓,然后就瘸了,不過被打以后倒是老實不少,每天也就安心過自己日子,喝酒理發,從另一個角度講他這日子也過得挺規律的。”
我聽完這人的故事后,點了點頭,覺得這人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只是日子過得比較瀟灑而已。
隨后,我們一行人各自上車,很快便分別了。
父親的車走到廣場那一塊時,我聽到車外傳來了陣陣撕心裂肺的哭號聲,其中還伴著一兩聲歌聲作為間奏,我看向窗外,只見又是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拖著一根斷腿走來走去,邊哭邊笑還唱著奇怪的歌,我好半天才聽出來,是我們這里祭祀儀式中用的一首悼亡歌。
“正月在街頭搞這樣一出,這人瘋了。”父親也看向窗外,笑著搖了搖頭。
我卻沉默著,看見他如同長街上唯一的舞者,在自己生命的舞臺上傾盡最后的力量。
他在哀悼什么,哀悼誰,我不清楚,我只看到他的生命窮剩最后的余火飄搖不定,他似乎開始解構生命中一切有意義的事物,最后發現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義,只剩下一個孤獨而不甘的靈魂,拼命在名為日常的池沼中不斷掙扎,最終行將溺死在一個稀松平常的下午里。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加密貨幣轉正!多米尼克立法確認波場系代幣為國家法幣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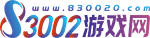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