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了個奇怪的借宿客。
雖然對于孩子們來說任何一個來這最偏僻的孤兒院投宿的客人都彌足珍貴,但是這個男人格外奇怪:他沒什么行李,只有一個掛在身上的口袋,衣物也并不厚重,長發的扎法是當地人從沒見過的樣式。腰間的佩刀是最特別的,雖然經歷了風沙和磨損已經結了一層薄薄的泥殼,但還是難掩它金色的光芒;刀柄上鑲嵌著的一顆寶石仍閃爍著古老的光輝,刀鞘上刻著的奇怪文字卻怎么也看不清了。
他本人也很奇怪,雖然從外表上看和當地人差別不大,身型只比常人高大一點,但眼睛卻格外大而明亮,目光不像其他借住的游客那般疲憊,反而十分銳利,仿佛一眼就能夠看穿世界的盡頭。
他剛一進門就被孩子們圍起來了,他們像一群小猴一樣興奮地攀上他高大的肩膀,好奇地抓他的頭發、踢他的靴子,年齡大一點的幾個孩子甚至還想抽出他的佩刀,努力了半天還是沒能拔出來便只好作罷。這個旅人倒是耐心,他也不生氣,就靜靜地等他們的興奮退潮,好像這是他最擅長的事。
過了一會我終于緩過神來,大聲呵斥這些小孩回想起禮貌,叫他們從這位客人的身上下來,去給他拿來吃的和熱飲——我不知道我剛剛怎么了。這個陌生人竟對我有如此的吸引力,讓我失禮地盯著他足足看了五分鐘,甚至更久。他笑著向我眨眨眼,表示感激。我們四目相對,我受寵若驚。
我同意了他的請求,他將在這個不大的孤兒院里借住一宿。
男人在孩子們吵吵嚷嚷的簇擁之下匆忙吃完了他的晚飯,他們不等他咽下最后一口面包就拉他到壁爐邊。孤兒院的小孩們從未見過這個村莊外面的世界,每一個來借宿的旅人都是他們初見世界的眼睛,他們像渴望樹莓果凍一樣渴望著每一位旅人的故事和他們身上獨特的配飾,甚至有時候還會趁客人們入眠之后偷他們的行李來玩,再在黎明到來之前放回原位。我對他們的這種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畢竟他們不會把任何東西據為己有,再珍貴的寶物也不過是他們一夜的玩具。只可惜碰巧能走到這里的游客并不多,所以每當有陌生人來叩響大門,我總會默默把孩子們當天的晚安時間推后一刻鐘,讓他們跟寶貴的客人多聊上一會,這也是我跟他們心照不宣的約定。我一邊在餐廳收拾餐具,一邊聽那些孩子嘰嘰喳喳地吵開了,七嘴八舌地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
“很遺憾,我剛出門不久,沒去過太多的地方,沒有什么見聞可以給你們講;至于我本人,也沒什么特別的。”男人笑著說,“但是我可以給你們講一個我在旅途中聽到的故事。”
孩子們眼里的光暗淡下去又被點亮,喊著好呀好呀,然后安靜下來。
“是一個哨兵,和一只鳥的故事。”
他們說大漠深處的戈壁灘上有一座城,它高高地佇立在斷崖之上,但卻是一座空城。沒有君主,沒有百姓,沒有罪犯,沒有商人,就像海上的一艘幽靈船。只有一個哨兵,他就那么站在城門之上,一動不動地守著這么一座空蕩蕩的沙城。他手握尖槍,定定地注視著大漠盡頭的某一個點,他是這座城唯一的哨兵。
他自己都不記得他是誰、這是哪、他的主人是誰,他甚至不記得他應該會衰老、死去、需要吃喝和休息,腦海里只有守城這個命令。他和這個沒有來由的命令、這座空空如也的沙城結在了一起,成了浮沉在時間川流之上卻永遠無法融化的一塊冰。
這座孤城不該有訪客的,直到那么一天。
“直到那么一天”,按理講這句話應該出現在一個人或者故事的轉折點,但這次不是。
那一天,他熟悉的那片天空中突然出現了一顆黑色的墨點。他第一次瞇起了眼睛,仔細聚焦著看一樣東西。這個墨點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上下起伏著,好像自己胸口的那顆東西一樣在昏黃的風沙里跳動著,越來越近。
那是一只鷹,但他并不認得。他一瞬間突然不知所措了起來,因為他只記得他的使命,卻完全不記得該如何完成他的使命了:它會入侵嗎?如果會的話我該怎樣阻止它的入侵?是要用我手上的長槍和腰間的利刃嗎?
也就是從這一瞬間開始,眼前原本熟悉的一切突然變得陌生而新鮮了起來。他沉默了不知多少年的腦子里面第一次有了回音,緊握著武器的手好像突然才生出了觸感,眼睛也因為聚焦而嘗到了干痛的滋味。風、沙粒、光線、心跳、血液循環,各種各樣的信息向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一股腦涌過來,他沒有辦法理解,但這些使他喘不過氣來,絲毫動彈不得。哨兵,這個連神都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人,因為一只鷹而變成了一個剛剛降生于世的嬰孩,而他甚至連啼哭都不會。
那只鷹越來越近了。看著這個會動的東西的輪廓一點點變得清晰、顏色一點點鮮明起來,他的這些奇妙體驗又慢慢緩和下來了。他靜下心來觀察它,先是看清了它不停鼓動著的兩翼,接著是金黃色的爪子和喙。最后它降落在了自己面前的城墻上,他也看清了它浮著光斑的眼睛。他伸出了右手,將手指搭在了它油亮的背上。這個神奇的造物——他在心里這么稱呼它——一動不動,任由他的撫摸,但并不看他。它盯著遠方的一個點,是荒漠之外的某個地方,那是它不惜穿越沙漠也要去到的地方。
他并不為它的獨特而感到訝異。在這片沙漠里他所見的一切都是獨一無二的,白天的太陽、晚上的月亮、日夜不變的這座城,還有他自己。讓他訝異的是它的存在本身,它不屬于這片大漠,但就這么憑空出現了。不,不是出現,是到來,從他所不熟悉的另一個世界穿越到了這個他熟知的世界中來。
他終于意識到了。雖然只有一點點,但他終于觸碰到了。
這塊茫然漂流了千萬年的寒冰,終于知道了整片冰川的存在。
他張張嘴,似乎想說什么,但只發出了一些奇怪的聲音,他只好又閉嘴。
然后他就和這只鷹就一直維持著這個姿勢,甚至沒留意日頭已經落了又升。
在第二天的晨曦里,或許是休息得足夠了,也或許是厭倦了,總之這只鷹終于動了,它鼓起那對有力的翅膀,鷹爪猛地蹬開城墻,呼嘯著向它一直看著的那一個點飛去。它離開得太快了,哨兵過了好一會才反應過來,撫摸了它一夜的手還停留在那個僵硬的姿勢。鷹離開時發出的那聲足以撕裂整片荒漠的嘶吼在空城里久久回蕩,哨兵目送著這位訪客掠過沙城的上空離開,看它一點點變回他們初見時的那顆墨點,消失在蒼白的日光里,心中生出陣陣滄桑的悲哀。
它一定不會再回來了,他想。但是他又覺得不一定。
它回來了。
這是不知道又過了多久的事,久到哨兵都以為他把它忘記了。這次它出現在晚上,黑夜把它藏得很好,它光潔如鏡的黑羽毛沒能反射出任何一絲光芒。不過哨兵還是發現它了,準確地說不是它,是它嘴里銜著的什么東西。它隨著那只鷹一起在夜空中起起伏伏,借著月亮那一點可憐凄冷的光閃爍跳動著,像一顆星向他飛來。
哨兵真的以為它為他銜來了一顆星。這個他唯一的、久別重逢的老友再次降落到他面前的城墻沿上,把嘴里的東西吐在了他的面前。那其實是一顆寶石。
如果他有一點想象力的話,他可能會猜測這顆寶石的來歷:可能是國王頭上王冠的一顆珠飾,可能是一個貴族青年拿來討好姑娘的玩意兒,可能是臭名昭著的珠寶大盜珍藏的贓物,也可能是某個窮苦人家里唯一珍貴的傳家寶。可惜的是對他來說,想象力是比這顆寶石更加珍貴和稀有的東西,他堅信這是夜空里的一顆星。他撿起這顆星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上左看右看,他被它從不同角度折射出的顏色各異的光迷住了。
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天上的那些東西一閃一閃的東西不光是白色的啊!他對自己說。
給他帶來這個禮物的那位朋友這次沒有看向它的目的地,它饒有興趣地看著這個人,看著他像只小獸一樣聞嗅、舌舔,兩根手指捏著那塊石頭在月光下左照右照。哨兵過了好久終于想起鷹,雖然他不懂道德,但他總覺得也應該送點什么給它才好。他想,既然它從天上來,給我帶來了天上的東西,那么我就應該給它一點地上的東西。于是他蹲下去仔細拈起一小撮沙子捧在手心,端到了它的面前。
孩子們都笑了,我也笑了。那個男人卻沒笑,他確實在很認真地講述這則傳說。
鷹居然接受了他的回饋。它沒有遲疑,把那一小撮沙子一下一下地啄掉,仰頭盡數吞下。然后它轉過身去,鼓起翅膀。哨兵知道,它又要離開了。
他沒有想要去阻止它離開。對他來說,鷹的到來和離開就像日月的輪轉、星辰的翻覆,不是他能夠也不是他應該控制的事物;但它又不同于日月和星辰,太陽落下月亮必然就會升起,斗轉星移也有著他能辨出的規律,只有鷹的來去跟任何東西都沒有關系,只有它自己知道它什么時候會來。所以他堅定地認為,這個神奇的造物,是比日月星辰更加奇妙和神秘的存在,既然是它自己決定了什么時候來,那么也應該由它決定什么時候走。所以他不為此感到失落。
不過他想起了鷹上次離開的時候發出的那聲長鳴,于是在它騰空而起之后,他也模仿著喊出了一聲凄厲的鷹鳴。他學得不錯,那只鷹回頭望了望他,用同樣的鳴叫回應了他,這一前一后的兩聲長鳴和鷹漆黑的身影很快被黑夜和空城吞沒,大漠又恢復了它到來之前的蒼涼。
他要繼續他的工作了。他和以往一樣站得筆直、一動不動,像座石碑。不同的是,他握著佩劍的左手里從此多了一顆天上的星星。
男人捧起盛著熱可可的杯子喝了一口,說,故事就到這里了。
孩子們很是不滿。“這個故事沒頭沒尾的!”幾個小孩開始帶頭抗議,“那只鷹又回來過嗎?”“哨兵呢?哨兵還在那片沙漠里嗎?他還在守著那座空城嗎?”
“好了,不要做討厭鬼,上床睡覺的時間都已經過了,快回你們的房間去!”掃興的人出現了。我像趕鴨子一樣把孩子們從大廳趕回他們各自的臥室。他們嘴里嘟嘟囔囔地偷偷說著我和那個講故事的人的壞話,但小孩畢竟是小孩,黑暗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好的鎮定劑,熄燈之后沒過多久就全都睡著了。
男人在廚房幫我提前準備明天的早餐。
“我沒有什么錢財,就只能這么報答您收留我過夜了。”他抱歉地笑了笑,“還有其他的什么活兒嗎?只要我能幫忙請盡管開口。”
我說,我想聽完剛才那個故事。
他撲哧一聲笑了:“我沒有講完這個故事,是因為結局實在不怎么美好。”
鷹最后一次來的時候姿勢有點怪。以往它飛翔時翅膀的每一下扇動都堅定而有力,讓哨兵覺得仿佛剛剛看到它的身影時臉上就吹到了它翅膀劃過來的風。這次它飛得歪歪扭扭的,甚至有幾次險些墜落。黃昏時刻,大漠的風沙已經停歇了,這個在血紅色夕陽中掙扎的黑色身影就顯得格外扎眼。
它幾乎是跌落在了哨兵的面前,把沙地砸出來一個小小的坑。它的胸口激烈地起伏著,大概是那一跌耗了它不少的力氣。哨兵不知所措地蹲下來撫摸著它,這才發現它的羽毛已經不再光亮,甚至有幾處已經脫落;鷹喙和利爪似乎也變鈍了,瞳孔里金色的光斑也模糊了。他隱隱感覺到有什么不對,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對,這又是他從未了解的領域了。
然后,有一個什么東西從它無力合起的嘴里滾落了出來,紅紅的、圓圓的,比哨兵的拳頭小上一圈。如果哨兵是這個世界上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一個人,那他都會認出這是一顆蘋果。垂暮的鳥奮力地用頭把那顆蘋果向他頂了頂,他順從地按照它的意愿把蘋果拾起來。他從沒吃過東西,但是水果成熟的絲絲甜味使他本能地狠狠吞了一口口水。
他甚至沒來得及再看兩眼就迫不及待地把它送進了嘴里。牙齒切開果皮的瞬間,清甜的汁水沖撞著流進了他干枯了千百年的喉嚨,果肉摩擦著他仿佛新生般柔嫩的牙齦和舌頭,然后兩者交融著沿著食道一路下行,“咚”地一聲,落入谷底。
他幾乎要被這一下擂昏了過去。
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整個的蘋果,連果核都沒有剩下,然后呆滯在原地,試著弄明白是什么東西正在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他從頭到腳的每一個角落,久久不能自拔。倒在地上的鷹靜靜地看著這一切,終于,太陽沉下去了。
他終于清醒過來,又俯身下去陪伴他的老友。可這時的鷹已經連睜開眼睛的力氣都已經沒有,月光下它胸口的起伏也愈發微弱。它奄奄一息,隨時都可能會死,但哨兵對此一無所知,仍是好奇地盯著它、不斷撫摸著它殘破的肉體,同時不斷回味著剛剛的蘋果。
一夜過去了,這只鷹居然仍舊頑強地活著。
當第一縷日光沿著地平線蔓延過來的時候,它突然睜開了雙眼,掙扎著站起來,撲騰著跳到了城墻外側的邊緣。它展開雙翼,用盡最后一絲力氣向外一躍而起,發出了一生中最凄麗的哀嚎。跟蘋果一般鮮紅的液體熾熱地從鷹撕裂的喉嚨中噴薄而出,在半空中開出了這片沙漠里唯一的一朵花。這只曾經美麗的鳥,在這朵花的擁抱中隕落了。
至于可憐的哨兵,他還在對著城門外那具鳥尸不斷模仿著鷹唳。
在連續三天三夜得不到回答的呼喚過后,哨兵終于下定了決心。他丟了守城的長槍,向著他的好友尸體所在的城外,義無反顧地跳了下去。
就在他跳下去的瞬間,身后的沙城突然開始崩塌了。哨兵聽到了身后雷鳴般的響聲,感覺到了崩裂的風席卷著碎沙強烈沖擊他的后背、灌進他的耳朵和鼻子,巨大的力量把他向前推,可他絲毫沒有向身后看,他全心全意地注視著那具鳥尸,一心向它墜落而去。
沙之城在它最后一聲低沉的怒吼中完全崩塌了,整片沙漠都被昏黃的風沙籠罩著。不知道又過了多久,一切的一切終于平息下來,這里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過。哨兵、鷹、沙城、還有他們的故事,全部都沒有了。
男人講完故事我們就各道晚安回了房間,但我卻遲遲沒能睡著。夜半三更,我昏昏欲睡,孩子們的房間里傳來一聲尖叫,我抓起披肩就沖了過去。他們點著小小的蠟燭圍坐成一圈,圓心中間的地上攤開一只打開了的行囊。借著微弱的燭光,我看到行囊里只有一樣東西。
那是一只早已經被風干了的,通身黑色的,鳥的尸體。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加密貨幣轉正!多米尼克立法確認波場系代幣為國家法幣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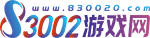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