鴨只要你曾經在一只天鵝蛋里待過,就算你是生在養雞場里也沒有什么關系。
如果根本沒待過呢?
沒有就沒有。
我曾經無數次從這個柵欄的破洞往外望,卻從未望見母親口中所說過的夏天的景象。大概是自我離開那個充滿溫熱的小巢起,季節就開始了更替,忠實而自我,沒什么東西能夠阻止時光的腳步。想到這里,我又一次抬起頭,可以看到農田的遺體正長著萋萋的草,滿目瘡痍,像是被手握著鋒利的銀色彎鉤的兩腳獸們所肢解成不甚規則的形狀,錯落在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間。與前幾次不同,這次我越過了這道屏障,從柵欄的尖端一躍而下,此刻,我站在農田的面前,期待著它的每一寸土地朝我撲面而來。
我感到新奇、興奮、自由、愉悅,唯獨沒有絲毫的恐懼,因為我是一只天鵝,我正在離開本就不屬于我的地方,僅此而已。
貓后來我離開了故鄉太久,把什么都給忘掉了。與其說忘掉,倒不如說,我不想再在心里自己給自己重復一遍那個異類是如何被種群反感,從質疑到排斥,最后到驅逐的故事,作為那只異類,面對族群的流言蜚語,我是無法反駁的——但我畢竟已經努力向他們解釋過了。
對不起,對不起,瞧我,還是有一提筆就開始自說自話的壞毛病,這不好,得改,就先從自我介紹開始吧。
我是一只不被同類承認的花貓。
自我懂事的那刻起,我就被告知,貓最多有兩種顏色,慢慢地,這句話的弦外之音開始無來由的在我耳邊奏響。
“三色的花貓,算不得是貓。”
至今我仍不明白兩件事,一是貓咪身上的三種花色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不只有我拎不清,天下的所有貓都不明白。二是我的同類為何會對我的花色抱有如此大的惡意,可能是貓這個種族繁衍至今,從未出過與我一樣的,有著三種花色的同類,因而三種花色的貓便成為了異類,異類便不應當存在于這世上。
那天傍晚下著小雨,我回到家,剛進門便看到父親守在桌前,母親背對著我站在墻角,一爪托起圍裙的一角,捂著口鼻,身影微微顫抖。
父親指指桌上的包袱,搖了搖頭。
那天晚上,父母一夜未眠,而我倒是倒頭便睡。父親雖未多言,但我已然明白,這個夜晚和以往的所有夜晚一樣,不會很長,太陽仍舊會照常升起,而夢醒之后,我便不會再擁有復睡的機會。天剛蒙蒙亮,家里便來滿了人,大長老坐在門廳中央,望見從屋里出來,背起昨夜桌上的那個包袱的我,清清嗓子,示意大家安靜,然后鄭重其事地調整坐姿,正襟危坐地把目光瞥向門廳一隅的我,緊接著,所有的人都將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恍惚間,我似乎看到他的嘴角揚起一抹笑意,那是一個不易察覺的,充滿挑釁意味的笑。
自走出族群的那刻到現在為止,縈繞在耳邊的父親的嘆息,母親的啜泣已經漸漸消失,一閉上眼,眼前便能看到的族內人到處飄蕩的異樣眼光也確實淡了許多,只要再這樣子,朝前走遠一些,我想我就能平靜地接受往事全然化作煙塵的那一天。
雨季這已經不知是我駐留在這個農場的第幾日了,我總在落著小雨的清晨醒過來,抬頭望,望到一片漫無邊際的,灰蒙蒙的天,沒有黎明時候的曙光,也沒有風,沒有掠過低沉的云的飛鳥,如果拋去遠處那幢大紅色建筑物里頭傳來的雞鳴,世界都是靜的,符合我心目中對雨季的全部定義。
雨水在耳邊流淌著,沖刷著我的三色毛絨,沖刷著我爪下的泥土,把本就艱澀難行的道路沖刷的面目全非。但對我來說,這種情況也算不得什么,比這更加糟糕的路我也走過,只要有終點,就能算是走得通的路。真正阻礙我前行的,是著青黃不接的時節里,包袱里的干糧早已被我吃空,因此我不得不停下來,和這個農場里的其他動物“愉快地”分享他們的食物。
作為外來人,我總是盡力與這里的原住民和平相處,期待著能把每次共同進餐的氣氛搞的稍微輕松愉快一些,奈何這些鄰居們卻根本沒有與我分享他們的口糧的想法,于是我便調整了策略,必須承認,這種策略雖然不甚光彩,但至少能讓我在逆境中不先被自己的胃袋擊垮。
場內似乎響起了嘈雜的聲音,聲音里頭混雜著許多音色各異但同等尖利的雞鳴。我循著聲音緩步前行,雙爪扒開叢生的雜草朝外看,兩群雞在我面前,圍著地上的一個鱔魚頭轉圈圈——似乎我的鄰居們很容易因為食物的歸屬權問題產生糾紛,而他們又不懂得解決糾紛的方法,兩群雞的首領各站一邊,左邊這方抖抖自己鮮艷的雞冠,右邊那方揮揮自己翎子上的羽毛。起初我還對這種場景感到新奇,但同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久而久之也失去了新意,何況我的目標也并不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只——目標就在地上靜靜趴著。
我從雜草里一躍而出,發出一聲尖利的喵嗚,露出貪婪的神情,朝著雞群飛奔過來。
頭雞看到了我,發出幾陣凄慘的哀嚎,狼狽的撲棱著翅膀,朝著紅色建筑物的方向飛奔而去,兩群雞頓時亂作一團,羽毛遍地,還沒等我跑到他們面前,幾十只雞便一股腦沒了蹤影,而我也并無追趕雞群的本意,四步并兩步,叼起地上的鱔魚頭,轉身朝著草叢飛奔,不一會把雞群憤怒的叫聲拋在了身后。
“嘎嘎,小偷,別跑,回來!”
這幫子傻瓜。
前天的半個豬肝,昨天的一串漿果,到現在嘴里銜著的鱔魚頭,屢試不爽。在個體數量上數倍于我的雞群被我用同樣的方法騙了一次又一次,卻仍不知道反思。在農場里過足了悠然愜意的生活的雞群,會對田野中一躍而出的陌生事物有本能的畏懼,而當這份畏懼化作在他們的眼前切實發生的現實的那刻,他們便會本能地逃避,慌亂中忘記了他們本有足夠銳利的爪子,足夠堅硬的能夠在我的身上開出幾個血洞的喙,也正因此,在這陌生的地界里頭,我并不敢有進一步對著雞群做文章的想法。
一溜小跑,鉆過分割農舍和田地的柵欄,朝著廣袤的田野飛奔而去,雞群的聲音已然消失不見。我隨口一丟,把戰利品甩到眼前的一塊石板上,正要低下頭大快朵頤之時,忽然覺得口干舌燥。好在雨季的緣故,野外的水源和食物相比,能用余裕來形容。我轉過身,越過幾個小草丘,便找到了我這段時間里經常光顧的那個漂浮著荷葉的小池塘,水面比昨天又漲起來了些,我趴在岸邊青青的小草上,豪壯地用舌頭舔水——我就是這個小池塘的主人。
喝飽了水,我便循著來時的路,慢慢走回藏著鱔魚頭的石板的地方,邊走邊想幾分鐘后應當如何美美地享用今天難得的一餐。
那塊擺著鱔魚頭的石板已經出現在我的視野里了,但我嗅到了一種奇異的氣味,氣味中有野生鳥類身上特有的那種腥氣,也有著農舍禽類走到哪里都帶著的干草垛的芬芳。我停下了腳步,想弄明白這種味道究竟來自于哪里。最終,我發現了那塊石板上站著,正在替我享用我的戰利品的不速之客。
好大的膽。
流浪者母親曾經講過,麥穗是在麥稈上長出來的,漿果是在灌叢中長出來的,她唯獨沒說過青石板上能生出什么東西——現在看來,我面前散發著誘人香氣的半圓形物體絕對不是從這塊石板上長出來的。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在啃這個憑空出現在我面前的叫鱔魚頭的東西的時候,絕對會啃得慢一些,這樣的話說不定能給它的主人多留下點殘渣,同時讓我用于狡辯的借口顯得稍微令人信服一點。
“先生,抱歉,我真不是有意的,我不知道這是您的東西,我太餓了。”鬼知道我哪里來的勇氣,我仰起頭,看向體型數倍于我,目露兇相的生物。
“餓?難道我不餓嗎?餓你倒是自己去找食物啊!為什么要把別人的鱔魚頭吃掉!”
面前的生物在朝我咆哮著,全身的每根毛都在暴怒的作用下兀自豎起,熱氣繞過尖利的獠牙,自他的口鼻中噴出來,彌散在雨霧里,好像在鬼鬼祟祟的燃燒。
“真的非常抱歉,我已經幾天幾夜沒吃過一點東西了,請告訴我,我該如何補償您呢?”
“那么,你就做好被我吃掉的準備吧,可憐的小鴨子。”他眼珠一轉,貪婪地用舌頭舔舔嘴唇。
“我不是鴨子!”他話音未落,我胸腔里居然平白生出一股無名的怒火,我昂起頭,死死盯著面前的未知生物的那張花斑遍布的大臉。
“你不是鴨子?開玩笑吧?”他把臉湊近我,用鼻子來回嗅嗅,不停地圍著我轉來轉去——母親的故事里似乎講過,獵犬打量自己的獵物的流程也是這個樣子。“我相信自己的判斷,你就是一只吃得太多,把自己養得肥肥的小黑鴨,別想騙我。”
“先生,我再強調一遍,我不是鴨子,我是一只天鵝。”
面前的生物瞪大了眼睛盯著我,隨即爆發出一陣歇斯底里的狂笑。
“天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你?一只家鴨居然說自己是天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簡直是我貓生聽過的最好笑的笑話!”他的笑聲回蕩在我的耳邊,我的喉嚨里似乎被塞進了一段枯枝,窒息而壓抑。
等等,貓生?
——先生,你是一只貓?
——不像嗎?瞧瞧,尖耳利爪,長長的尾巴和獠牙,我有哪一點不像貓嗎?
——可是你的身上,你的身上居然有三種顏色。
他臉上的笑意瞬間一掃而空,劍眉暴豎,殺意自深棕色的眸底向我刺來。
——三種顏色不可以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每根毛發都燃燒著。
——先生,也許我說錯了什么話,但是我自從蛋殼里頭生出來的那一刻,母親便告訴我,全天下的貓類,身上最多只有兩種顏色而已,請您不要生我的氣。
我看到他渾身豎起的毛發慢慢歪下去,怒火燃燒的余燼從他的眼眶中飄散。
“你是對的。”他說著轉過身去,聲音平淡如水,在雨霧中凝結起來。
“當然,自我離開母親身邊,走出森林,走過濕地,從農舍的柵欄里翻出來,直到見到您的這刻為止,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三色的貓,如果我早些見到您,我便知道即使是母親說過的話,也不一定完全正確了。”
“你的意思是,你相信我是一只貓嗎?”他再次轉身,瞳孔興奮地閃動了一下。
“為什么不能相信呢?母親還說過,貓不僅是我們的天敵,還是所有鳥類的天敵來著,貓捕食鳥,是他們的本性,而您剛剛說,想吃掉我,現在除去花色不同這一點外,您倒是符合貓的全部特征了。”
他笑了起來,長長的胡須順著臉頰在空氣中抖動。
“小鴨子,你很有意思,我決定不吃你了,你在我變心之前,抓緊離開吧。”
“先生,我不是鴨子,我是一只天鵝,一只天鵝。”
“小不點,不要再說怪話了,你就是一只長得比你的同類稍微壯碩一些,毛色湊巧是黑色的鴨類罷了,你為何那么執著地認為自己是天鵝呢?瞧瞧你的樣子吧,臃腫、丑陋,羽毛連家鴨的光澤都沒有,脖子上還有一塊奇丑無比的綠斑,一直延伸到頭頂上。快滾回你的農舍去吧,野外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請您相信我,我是一只天鵝。”
“……”
黑天鵝那天,我和這只偷吃了我的午餐的小不點一起在農舍的屋檐下躲雨,天色愈發昏暗,雨倒是愈下愈大,屋檐外的一切被雨水弄得靜悄悄的,遠處的山巒的輪廓也被雨水浸潤得愈發模糊,直到無聲無息地和夜色融為一體。
我倚在窗邊的木框上瞇縫著眼,瞧著黑油油的,探著脖子朝窗臺外頭看的小不點,一小時里,他已經往外頭看了不知多少次,我能感受到來自他身上的焦躁不安。
“嘿,雨越下越大了,今晚就在這里住一晚吧,明天一早再出發,我的探險家。”
“先生,您還沒回答我呢,您說您見過天鵝,天鵝到底是什么樣子的?”
“這已經是你今天第四次問我這個問題了。”
“您再給我講講吧,越詳細越好。”他看向我,黑瑪瑙般的兩顆眸子里閃著興奮的光。
我確定我是見過天鵝這種高潔的鳥類的,但我從未有過近距離接觸他們的機會。在我算不得短的流浪旅途中,離他們最近的時候,便是看著他們排成整齊的陣列,從我頭頂上碩大的天幕中撲扇著翅膀飛過去。
“羽毛潔白無瑕。”
“這個您說過。”
“呃……嘴巴是紅色的,就像……”
“這個您也說過了。”
“頸部修長,昂然如玉。”
“您也……”
“那沒了,我的探險家。”
“您再仔細想一想嘛,求求您了,哪怕是再多一點點的細節也好,比如說,小的天鵝是什么樣子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嗎?”
“聽著,我的小探險家,你給我仔細想想,”我被他問得有些不耐煩。“你明明知道,鳥類和貓類是不共戴天的仇敵,那么我怎么可能有機會去貼近天鵝們的巢穴?”
“那也就是說,您也不知道,小的天鵝是什么樣子的了?”
“或許,我不用知道小的天鵝是什么樣的,單看你的外貌,哪點和天鵝沾邊了啊?你不會是想告訴我,你毫無依據地稱自己是天鵝的舉動,僅僅源自于你自己給自己編造出的一個瘋狂的念頭?”
小不點竟然漲紅了臉。
“我才沒有!我破殼的那天,就與兄弟姐妹們截然不同!母親說,我不是家鴨,我是她從野外撿到的一枚天鵝蛋里孵出來的!”
“嗯,所以你真的信了,對嗎?”我不置可否地看著他。“你有沒有想過,也許是你的母親為了維護你的自尊,怕你想不開,不敢承認自己的缺陷,所以給你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呢?”
“不可能!母親絕對不會騙我!母親常在我的兄弟姐妹們入睡之后給我講起天鵝的故事,她說,小天鵝們和我一樣,都長得丑陋無比,羽毛晦暗,體態臃腫,但是當到了春天,冰雪消融的時節,我也會變成你口中的,能夠自由翱翔的天鵝!”
“嗯吶,所以,你為什么一個人出來流浪呢,還不是被你的族類拋棄了。”
“哪里有拋棄一說!他們是鴨子,我是天鵝,我終有一天會找到我自己的族群,先生,如果您不信的話,就請你瞧好吧。”
“聽著,小不點,我對你的遠大理想沒有任何興趣,在我看來,我完全不可能把面前的你和那些高大雍容的鳥類聯系到一起,我只是一只普普通通,居無定所,隨風漂泊的流浪貓罷了,短時間內我不可能離開這個農場,你要走的話,明天天一亮,便離開好了。”
日落,月升,雨終于小了,天幕上升起繁星點點。
“魚頭的事情,還是多謝您的原諒,您真是一只大度的花貓。”話音落畢,他把自己縮成一團毛球。“也許母親說的一些事情也不完全正確,比如說,我一直篤信貓與鳥類不共戴天,直到遇見了您。”
“你不是很篤定你母親的話么,那么,為什么偏偏把對貓的定義排除在外頭了?”
“因為母親說眼見為實,而我已然見過您這只三色的花貓。”
我一夜未眠。
獵犬從那日清早起到今天,我已經尾隨在小不點后面整整三十個日夜了,這段時間說長算不得長,但已然足夠把四季的指針向著冬的方向撥動極大的幅度。我和他保持著相當的距離,確保他不會脫離我的視野的同時,又很難發現我在悄悄跟蹤他——這是貓的特長。你問我為什么要這樣做,咳咳,我只能說一句,無可奉告。
必須承認,小不點的確不像是農舍里偷偷溜出來的家鴨,似乎在野外生存這方面,他已經有了長足的經驗,儼然不像是剛剛從蛋殼里鉆出來,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的新手。他會利用清晨荷葉上的露珠解渴,會從相對干燥的沙地上掘出青蟲來果腹,會在聽到天空中凄厲的鷹唳的剎那鉆進枯葉堆里。除了昨天游過那個鱷魚偽裝得極妙的小湖時發生了一段有驚無險的小插曲之外,倒是沒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了,鱷魚悄悄地朝他游過來,我從小湖旁的樹上踩下一節枝條,枝條砸在水里,翻騰出帶著氣泡的漣漪,鱷魚一驚,半截吻露出水面,小不點這下子看了個清楚,滿頭大汗地游上岸,那鱷魚抬頭死死盯著我,我在樹上朝他眨眨眼睛,抱歉啦,你不能打他的主意。
這些日子里,我看見他主動和蘆葦蕩中的野鴨搭話,主動同森林中的松鼠分享吃食,甚至有時能和土中鉆出來的土撥鼠交上朋友,但無一例外的,談話在自我介紹時總是會碰壁,沒有一個人愿意相信他那套關于自己是天鵝的說辭。
大雁的譏笑,野鴨的嘲諷,當他路過其他的農場的時候,母雞也能抓住機會狠狠地笑罵他兩句:“要不你就接受自己是一只畸形的鴨子的事實吧,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留在我們這里,看看能不能產下幾個蛋,只要你不和我們這里的母雞們結婚,農場主不介意多添一張嘴的飯就是了,咯咯咯!”
可他沒停。
他一直在走。
冥冥之中,他好像知道自己要往什么地方去。
有時候我會趕到他前面,偷偷地看他的臉上是否有絲毫的黯然和神傷,但每次看到的,都是一張平靜如水,毫無波瀾的面龐,我搞不懂,這種自信到底來自于何方,真的會有這種從未接受過任何肯定卻毫不動搖的動物嗎?
恍惚間,他那雙瑪瑙般的眸子里一閃而過的亮光讓我想起那無數個日夜里,我做過的關于我自己的夢,夢里我經常看著湖面上倒映出的自己,看著那三色的花紋,心中翻騰起悲傷的種子。但旋即我又覺得,那些時刻總歸是夢,現在現實就在我面前擺著,我睡去的太久了。
不知何時,面前出現了一條寬敞平整的大道,由于氣溫下降的緣故,路面被凍得堅實許多,正是好走的時候,因此我十分不理解前面的小不點突然離開這條路,拐向旁邊的一塊巨大的沼澤地的舉動。不多時,沼澤地里傳來的聲音打消了我的疑慮。
小不點一聽到那些和他類似的禽類發出的聲音,就會變得興奮異常,主動去尋找聲音的來源,這在我看來不是個好習慣。
這片沼澤地里生長著大片的蘆葦,隨著吹過的風搖曳著,小不點就這么跳進了泥水里頭,朝著發出聲音的蘆葦蕩里游過去,黑黑的身軀后面劃出一行白色的泡沫,很像過段時間之后就會從天空中飄散而下的雪花堆積起來的道道白痕。
貓天性畏懼水,除了飲水之外,一般不會靠近這種地方半步,可我根本不知道小探險家闖入這片沼澤的用意,我只得跑上一邊的斜坡,悻悻圍著岸邊轉悠,觀察著他最終會從哪個方向鉆出來。
這片沼地四面被隆起的土坡環繞著,從這上面看,整片蘆葦蕩的情況都盡收眼底,難怪會有禽鳴聲,原來這里是一片候鳥越冬的棲息地,不時有身影從天空中落進蘆葦里頭,也不時有身影從蘆葦中直沖云霄,可我還是沒發現小不點跑到了哪里。我揚起頭,用鼻子猛嗅周圍,粗野的腥氣縈繞在鼻尖久久不散,他身上的氣息也混在腥氣和水霧里,令我難以分辨。
與此同時,蘆葦蕩的側面的陰地里悄無聲息地出現了一個人影,人影后頭跟著另一團影子,緊貼在地面上,沿著蘆葦蕩的邊緣移動,速度快得出奇,當兩團影子走到陽光底下,我便看清楚了,那是條身形魁梧,皮毛發亮的獵犬,一陣風從我身后吹過,我趕忙趴下,整個身子伏在地上——如果讓那只犬嗅到我的氣味,那我今天便兇多吉少。果不其然,那只犬扭頭面朝我藏身的方向望了望,即使我的反應已有如此之快,他肯定還是聞到了什么。可當他想朝我的方向多走出幾步的時候,身后的人跺一跺腳,他便扭過頭,趴在人的身前,眼睛從小山坡上重新聚焦到蘆葦蕩里。
砰。
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
砰。又一聲。
我眼睜睜地看著剛從蘆葦中起飛的兩只野鴨身上爆出通紅的血霧,而后直挺挺地落到沼澤地里,把水染得鮮紅,我看到那個人的手中不知何時抬起的棕色長桿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長桿一端裊裊吐出的青煙里,刺鼻的煙火味和焦味敲著我的天靈蓋。
震耳欲聾的巨響沉下去,平靜的蘆葦蕩里便熱鬧起來,我看著根根蘆葦桿被受驚的鳥類們在慌亂中折斷,燈芯草也向兩邊倒去,那只獵犬抓住這個空檔,瞬間沖進鳥類的世界里,一時間狂吠,哀鳴攪在一起,空中不時飛起身形各異的鳥——大雁,野鴨,斑鳩,還有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物種。
等等。
那是?
那該不會?
白的發亮,翅膀修長,頸部溫軟如玉,眼睛深邃透亮,嘴部半黃半黑,黃里透出點紅,如琥珀里點了胭脂。
天鵝,好多,好多天鵝。
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觀賞這種傳說中的鳥類。他們不慌不忙,成群結隊地起飛,似乎在嘲諷著兩腳的偷襲者,我看著他們在我面前騰空而起,撲向天幕,像朵朵白絮乘風漂流。
每次巨響響起時,天空中的鳥類便要落下來幾只,但唯獨天鵝們。
不慌不忙,成群結隊的起飛。
騰空而起,踏入云巔。
那是他們的舞臺,他們本就沒有什么可畏懼的。
和那些亂作一團,撞個滿懷的鳥類不同,天鵝們總會先離開蘆葦蕩的深處,在離水邊不遠的岸上集結起來,再撲扇起翅膀,局促逼仄的地方也確實是容不下這些高潔的鳥起飛的。我不由自主的立起身來,一步步,挪到離他們近一些,再近一些的地方,看著神話般的鳥類在我面前騰起,潔白的羽毛將一切光亮匯聚,投入我的眼底。
小不點重新出現在我視野里的那刻,我遠遠的看到,他似乎在跟著蘆葦蕩里最后一只天鵝的步伐奔跑。
他面前的天鵝奔向大群,一同他奔向的地方。
他的身后,那只獵犬的眼睛閃著紅光,朝著他的方向撲殺而來。
他們的距離正在一點點縮小。
天鵝奔向岸邊,舒展翅膀,躍向水面,蹼尖輕輕掠出幾道水紋,寬廣的雙翼便將他托起。
小不點也學著天鵝的樣子,朝著水面躍起,但他身后的獵犬似乎比他躍得更高,魁梧的身體在他的頭頂投下死亡的陰影。
砰。
獵犬躍起的軌跡在空中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巨大的身影一個趔趄,當劇痛從我的頭頂傳到全身時,我便知道我拼盡全力的一擊的結果已然如我所愿。身型上的巨大差距已然斷絕了我戰勝這只散發著殺意的犬的全部可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幫那個自稱是天鵝的笨蛋多拖延一些時間,讓他跑的越遠越好,所以我選擇主動撞向這只犬。
獵犬的余光掃到了我的身影,我們的目光在空中交匯,而后,他從容穩住身姿,平穩著地,我則四腳朝天,重重地砸在沼澤里。
當我掙扎著站立起來的時候,獵犬的爪子已然重重擊打在我的腹部。
“你是誰?為何要主動攻擊我?”他的聲音像是石頭。
“我是誰,與你又有何相干?”我忍住劇痛,揮動爪子,在他的臉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吃痛,爆出一聲恐怖的咆哮,我能感到他的牙齒嵌入我的身體,我像一塊被雨水漚爛的木板被他輕松拎起來,重重甩到沙礫遍布的灘涂上,砸的我眼冒金星。
這是種族基因帶來的絕對的、懸殊的力量差距。
我直挺挺地躺在冷冰冰的沼澤地里,熱辣的酸流從我的口中涌出來,耳廓中獵犬向我走來的腳步聲愈發清晰。天鵝群聚集成巨大的云朵,從我的上空飛過,他們也許看不到這血腥的一幕,但我很明白,到此刻為止,我已經成功的完成了我算不得長的一生中的全部試煉,到了與世界告別的時候了。
恍惚中,我似乎看見空中那朵巨大的白云里冒出來一個黑點,說不通是什么地方冒出來的,一時圍著云朵打轉,一時鉆進云朵里面,再從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鉆出來,就這樣不斷穿梭著,隨白云一起飛出我的眼眶,冥冥之中我覺得很像我遇見過的某只自稱是天鵝的小不點。
失去意識前的最后一刻,一聲尖利的口哨響起,獵犬的氣息在我四周倏然消失不見。
我們時隔四年,我重新回到了印象中的這片沼澤,一如四年前,它靜靜地待在大路旁邊,蘆葦叢生,高高的隆過水面,禽鳥仍舊藏在里頭尋找著食物,灘涂上的蒲公英短暫生長,孕育出的種子隨風飄揚,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又似乎都面目全非,眼前的景象混在記憶中的剪影里,有琳瑯之感。
四年里,我去過很多地方,看見洪水漫灌巨浪滔天,看見礁石流金寸草不生。看見許許多多形色各異的生物,其中當然也包括不少同類,說來也奇怪,記不得是從哪一天起,我遇見的貓看到我之后先是瞪大眼睛,再對我的毛色贊不絕口,問及原因,原來是三色的公貓極少,全族上下也沒有幾只,用他們的話說,是萬里挑一的珍稀物種,當我聽到他們說“如果我和你一樣天生三色就好了”之類的話時,總是報以爽朗的一笑,然后友好的和他們分別,再繼續流浪。
我并非不關心族群的現狀,每當我萌生回家看看的想法時,有個長得丑陋,粗笨,暗啞,臃腫的,自稱是天鵝的小不點的身影便同時從我眼前劃過。是啊,要說我今生遇見的最奇特,最搞笑,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生物便是它了,他居然說自己是天鵝。
那個深秋的傍晚,我在這里被濃重的暮色嗆醒,身邊沒有獵犬,天空中亦沒有任何鳥類,只有一身哧哧作痛的傷痕讓我明白,此前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夢,而那只黑色的小不點究竟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烈日當空,初夏的熱浪漫過土丘,熱騰騰的從我的身上蒸騰過去,我回到灘涂旁邊,四下張望,找到一株灑下方寸陰涼的垂柳。當我走到樹邊上的剎那,不由得尖叫一聲,向后退出老長的距離。
隱匿在陰涼里的生物似乎被我發出的聲響驚擾到了,他猛地抬起頭,打量著退出好一段距離的我,我看明白了,這是只犬,該死,我的運氣真好。
我們就這么隔空對視著,半晌,我似乎覺得我在哪里見過面前的這張臉,當我正在懷疑我是否看走眼的時候,他的聲音先穿透了夏日的熱氣。
是你?
是你?
他站起來,我也停止了后退,似乎我們都記起了四年前的那次邂逅,他臉上的那道血痕仍舊觸目驚心。
不久,我們一同躺在樹下的陰涼里。
“給我講講吧,稀有的物種,那天你為什么要主動妨礙我?”
“你先給我講講,當時為什么留了我一命?”我看到他臉上浮現出的曖昧的笑。
“那只是你運氣太好罷了,小子。”
那聲口哨,對于一只獵犬來說,是如山的軍令,無論他身處何方,聽到主人的召喚,便要迅速回到主人的身邊。那日,他的獵人收獲頗豐,因此早早結束了狩獵行動,帶著他離開了這里,估計那個人類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無心之舉硬生生地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
“明白了吧,小子?該你和我解釋解釋了。”
“對不起,我只是不想讓我的朋友死在你的嘴下。”我思考良久,做出了這個并不能令他滿意的回答。他眉頭皺了起來。
“你的朋友在哪里?那天,我記得我和我的主人是來獵鳥的,難道你的朋友是只禽類?”
“確切的說,是只……天鵝。”
“和禽類交朋友的貓,真是不可思議。我確實追趕過一只白色的天鵝來著,要不是他前面有只通體黑色的烏鴉擋著我的路……”
“啊,糾正你一下,你口中的烏鴉,就是我的朋友。”
“你在耍我嗎?那明明是一只烏鴉啊?你覺得他哪一點像天鵝了?”
“萬一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通體黑色的天鵝呢?”我不由自主蹦出這么一句。“比起這個,你剛剛說,你的主人?那個獵人在哪里?”
“沒啦,早沒了,就在那天結束后不久,我就自由了,獵犬的隊伍里不需要年事已高的犬。”
我翻過身打量他,他的目光仍舊矍鑠,但已然和幾年前判若兩犬了。
“所以……你現在要……去哪里?”剛一開口,我便覺得我自己很沒禮貌。
“流浪,去任何地方,看看我沒看過的東西,然后到走不動的那一天,在不為人知的荒野里給自己準備一個永遠的家。你呢,珍稀物種?”
“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想回家看看……”
“有家好哇,不管怎么說,有家就是要回的啊,我出生的那天起,就接受高強度的訓練,搞得我現在都不知道生我的父母是誰,家在哪里就更不知道了。”
“抱歉,讓你想起這些。”
“喂喂喂,真正應該道歉的,是你在我臉上留下的這道疤,好吧!”他沖我呲牙,故意把眉毛豎起來:“不過,我那天也下了死手,這么一看,似乎是我欠你的更多一些,道歉的話要先讓我來說。”
“不必,你也是履行作為一只獵犬的職責罷了。”
“如果真如你所說,那只烏鴉是你的朋友,那你撞我的那一下也理所當然,這樣,似乎我們都沒有什么錯,我們算扯平。”
我們的對話在天空中傳來的一陣喧囂中結束了,我倆抬起頭望天,越冬的鳥類正成群結隊的飛回棲息地,這片沼澤也忠實地履行著中轉站的職能。
老獵犬指著天,給我講這些鳥類的物種,作為經驗豐富的獵手,他面對這些曾經的獵物們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那群栗褐色,頭上有星或者菱形標記,眼角有白色細線的,是水鴨。
……
左邊那只叫做灰雁,右邊那只叫做白額雁,毛色有時候差不多,千萬別搞混了。
現在飛過天上的這一大群白色的,喙上有幾種顏色的是……
“我知道,是天鵝。”
“沒錯。”
“等等……那是什么?”我用手指著空中的一個灰色斑點。
“怪事……天鵝們怎么會跟著一只綠頭鴨飛呢?”他站起來抬頭望。
“你說什么?綠頭鴨?就是現在飛在天鵝群最前面的這一只嗎?”
“是啊,綠頭鴨,野鴨的一種,我們這里不怎么常見,從頭到頸部,全是綠色的,胸脯是玫紅色的,也是擅長長途飛行,能飛得老快老高的禽類,除此之外還擅長潛水……我曾經見過這小東西從蛋里生出來的樣子,渾身黑油油的,和現在天上飛的完全不一樣,要非說有什么辨認方式,可能就是生下來,頸部可能會有一抹不易察覺的墨綠色絨毛吧。”
老獵犬的話沒說完,我便站起身,跑出了柳樹下的陰影,邊跑邊沖著天空中飛過的天鵝群嘶吼。
小不點,我在這里,我在這里。
天鵝群的首領似乎聽到了我的喊叫,他低下頭看著我,瑪瑙般的眸子里,閃動著熟悉的光。
時光荏苒了幾個輪回之后。
我再一次和他對視。
“你,成功了,對嗎?”
[責任編輯:linlin]
相關文章
- 加密貨幣轉正!多米尼克立法確認波場系代幣為國家法幣
- 蘋果今天發布了 Safari 技術預覽版 156 更新-世界熱資訊
- IBM 今天發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新要聞
- 一加 Ace Pro 原神限定版發布會將于 10 月 24 日 19:00 召開-焦點資訊
- Netflix 今日公布了該公司的 2022 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全球今亮點
- DLSS 功能測試已支持英偉達 DLSS 3 和 DLSS 幀生成-全球時訊
- 王子睿不斷接受挑戰,雖然是個好演員,卻還需要一定的機會-天天微資訊
- 宋昕冉:變個身,今天是眼鏡娘-世界要聞
- 總裁夫人也缺錢?47歲金巧巧直播帶貨被質疑,“無聊玩玩而已”-世界微動態
- 港星罕見合照,周潤發和林青霞貼臉留影,真是甜蜜萬分,情懷爆棚-視焦點訊
- 梁朝偉撥通已故張國榮電話,電話里真的傳來了聲音,嚇得他七天都沒緩過來-全球簡訊
- 雷軍:小米成功的唯一途徑是成為電動車前五,年出貨量超過1000萬-每日精選
- 2022年,你身邊的「王者榮耀」玩家變少了嗎?-天天觀焦點
- 騰訊市值再度超越茅臺:排名中國上市公司市值首位-焦點日報
- 馬斯克稱特斯拉市值或超4萬億美元-環球觀天下
- 高等數學(上)習題課第四期10月20日19點上線 山東財經大學副教授宋浩帶你玩轉函數-當前要聞
- 鄉村振興|陜西:漢江漁民開啟農旅融合新生活-最新快訊
- 杭州市住保房管局與貝殼找房結對共建助力新時代文明實踐
- 植宗山茶油發布便攜系列 讓生活與健康無縫銜接
- 你喜歡吃蔬菜嗎?這些蔬菜味道雖重但是營養豐富哦~
- 金秋時節正是吃板栗的好時候 吃板栗記住這些禁忌
- 天聊 | 傳遞生活力量,收獲溫暖瞬間!
- 東方神起:35歲的沈昌珉當爸爸!粉絲:初代偶像,又驕傲又悲傷!-熱門看點
- 林志穎妻子回應6歲兒子車禍后第一句話,聽到真相時忍不住哭了。-快消息
- 《王國》后,金銀姬編劇又出新作!恐怖懸疑!-環球報資訊
- 白鹿王鶴棣以愛為營內容大變買個ip網劇套原創劇利用書粉基礎宣傳-全球聚看點
- 蘇感加倍來襲,養成系年下弟弟吳磊A氣十足!-全球最資訊
- 獨家|羅永浩將于天貓雙11預售日10月24日進行淘寶直播首秀-環球新資訊
- 養生俗語“女三熱 男三冷”是何意?你知道是哪三冷三熱嗎?
-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凍三候雉入大水為蜃 冬天多喝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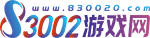 評論員文章
評論員文章










